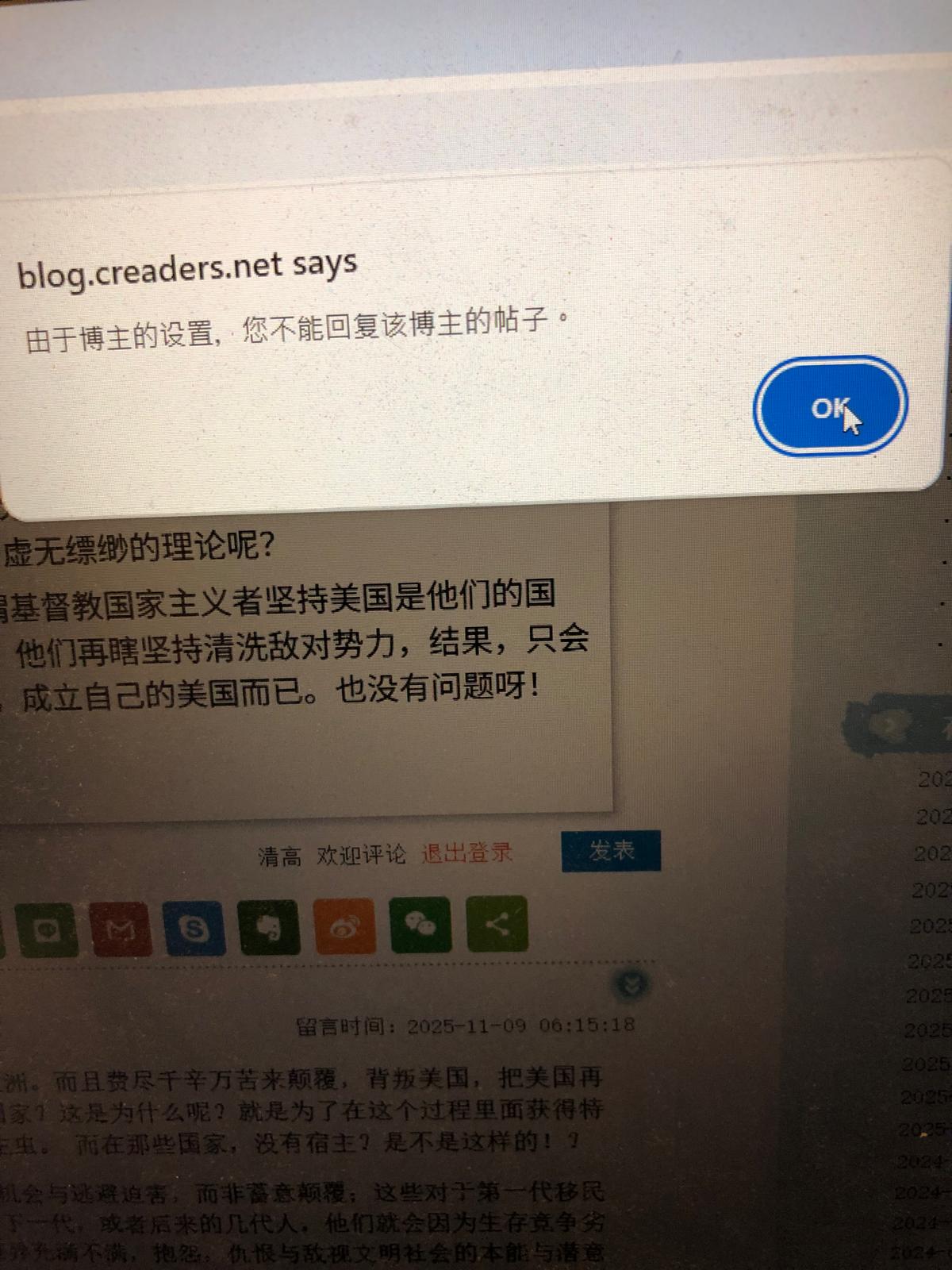赵晓:从“包容性增长”与“代际契约”看资本主义
作者:赵晓
一、资本主义的裂缝:年轻人为何不再相信未来
2020 年,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写给扎克伯格等 Facebook 高层的一封内部邮件中提醒道:
“当 70% 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自称支持社会主义(socialism)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愚蠢或被洗脑,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
蒂尔的答案非常直白——
学生债务(student debt)过高,
房价(housing cost)过高,
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之外。
当他们没有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份”(stak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如此,他们自然会反过来与之为敌。
这封信揭示了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
一个“代际契约”(generational compact)的断裂。
二、“代际契约”的破裂:从机会社会到封闭社会
所谓“代际契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隐性支柱。
上一代通过制度与市场创造机会,
下一代通过教育与劳动实现向上流动,
社会由此形成一种持续的信任循环:
勤奋与储蓄会有回报,投资与创新能被分享。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找到一份普通的工厂或公司工作,
年薪约为 4,000 美元——而那时一套郊区独栋住宅的平均价格是 9,000 美元。
换句话说,只要工作三年、略加储蓄,就能买房成家;
一对夫妻可以靠一份收入养活全家,孩子的学费几乎全免,未来是可预期的。
学界普遍认为,从 二战结束(1945)到19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最繁荣、最稳定、最具包容性的阶段,被称为: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或 “The Great Compression”(财富差距大幅压缩时期)。
这一时期有几个鲜明特征:
1.经济增长持续高企。
1945–1973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4%,远高于20世纪平均水平。
制造业繁荣、出口旺盛、就业充分。
2.中产阶级的壮大。
普通工薪家庭凭借稳定收入即可买房、供养子女上大学、享受医疗保险。
美国社会第一次实现了大规模的“中产化”。
3.财富与机会的相对平等。
这一阶段,美国的收入差距是20世纪最小的时期。
《财富》杂志称那时是“一个每个孩子都能想象更好未来的时代”。
4.教育与住房的普及。
政府推出了“GI Bill”(退伍军人法案),让上百万退役军人获得免费大学教育与住房贷款——
直接催生了战后“婴儿潮中产阶层(baby boomer middle class)”。
换句话说,那时的资本主义兼具“增长”与“包容”,
因此,也赢得了人心。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美国知识界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困惑: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这也是德国裔社会学家 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 早在 1906 年写下的一本经典著作。
他观察到:在欧洲,工人阶级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但在美国,却始终没有形成类似的政治潮流。
松巴特的结论极为著名:
“因为美国的工人忙着吃牛排(beefsteak)。”
他的意思是:
美国的资本主义太成功、太务实、太有“向上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工人阶级没有被彻底剥夺,也因此不容易形成革命性的阶级意识。
换言之,资本主义自己消化了反资本主义的能量。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繁荣在 1970年代石油危机与1971年美元脱钩 后逐渐结束。
制造业外移、金融化上升、全球化加速——
美国进入所谓 “Neoliberal Era”(新自由主义时代)。
从此:
·工资停滞,生产率继续上升;
·财富开始向资本端集中;
·教育与住房成本飙升;
·年轻一代首次面临“生活不如父辈”的现实。
特别是,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代际契约”更是进一步瓦解。
教育通道失灵。 高等教育成本飙升,学位贬值,年轻人以负债进入社会。1950年代,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可以靠父母的工资上大学;今天,一个同样的孩子,即使拿到奖学金,也往往要背上三四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当年的大学是通向中产的桥梁(bridge to the middle class),如今却成了进入社会的枷锁(debt trap)。
住房市场垄断。 房价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房地产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围墙”。 在上世纪中叶,一个工人家庭三年积蓄就能买下一套郊区小屋;而今天,在纽约、旧金山或伦敦,一套普通公寓的价格是平均年薪的十倍以上。于是房子从“家的象征”变成了“金融资产”;居住权从生活权利变成了投机筹码。父母一辈靠工资买房,孩子一辈要靠父母买房。他们被称为“租房世代(generation rent)”,房地产成了一个财富循环的封闭系统(closed wealth loop):旧有资产升值产生更多资本,新的进入者再也无法跨过门槛。
资本结构固化。 资产型收入取代劳动型收入,财富继承胜过个人奋斗。在战后黄金时代,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能与生产率一起增长;而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生产率上涨了七倍,工资却原地踏步。与此同时,股市、房地产与金融资产却节节攀升。富人靠“钱生钱”,穷人靠“命换钱”。资本收益(return on capital)全面超越劳动收益(return on labor)。而这场游戏的最大赢家,并不是最勤奋的人,而是最早上车的人——或者说:出生在资产的一边的人。财富不再来自努力,而来自继承;奋斗不再能改变命运,而只能延缓落差。
于是,原本开放的“机会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
正在滑向一种“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
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体系之外,
而老一代在资产增值中不断“垒高城墙”。
于是,到了 21世纪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
他们已经不再拥有父辈那种对资本主义的信任与参与感。
这也正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那封信所提醒的历史回声——
“当年轻人被排除在资本积累之外,他们就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
三、“包容性增长”: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呼唤
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证明它不是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药方。然而,要修复代际契约,资本主义必须重新学习“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种超越单纯 GDP 的增长理念,强调增长的成果应惠及更广泛人群,尤其是弱势与年轻群体。它是“文明性增长”的基础环节。
包容性增长并非平均主义或再分配神话,
而是强调增长的成果应被更多人分享。
它要求市场、制度与文化层面共同转型:
1.在市场层面 ——
建立更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让劳动、创新与创业者获得合理回报,而非被垄断资本吸血。
2.在制度层面 ——
降低教育、住房与创业的门槛,让年轻人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参与财富积累。
3.在文化层面 ——
重建对“未来”的信任。资本主义若不能让年轻人怀抱希望,它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正当性(legitimacy)。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明问题。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证明,没有“包容性增长”,国家就会失败,资本主义将沦为权力与资本的循环机器。
四、文明的拐点:资本主义的救赎在于自省
蒂尔的洞察可视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次内部忏悔(internal repentance)。
这位自由市场的信徒没有转向社会主义,
却承认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它的“道德契约(moral compact)”。
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自我修复能力;
而它的危险,也正在于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
当市场只剩“赢家通吃”,当年轻人再无“入场机会”,
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信任的制度,而变成焦虑的陷阱。
真正的“文明性增长”(civilizational growth)必须超越利润逻辑,
它要重新建立三重契约:
对人的尊重(Human Dignity);
对代际的责任(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对社会的公义(Social Justice)。
五、结语:没有希望的资本主义,必然引发危机
从彼得·蒂尔的邮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硅谷的焦虑,
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镜像。
资本主义不是天生邪恶,也不可能完美,
但若拒绝更新“包容性增长”的伦理与制度,
它终将因代际绝望而坍塌——纽约变天就是一个信号。
而当代中国,同样面临两极分化与“代际断层”的挑战。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简单模仿或批判任何体系,
而在于在信仰与制度之间重建希望的契约——
让每一代人,都能相信努力与善仍然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