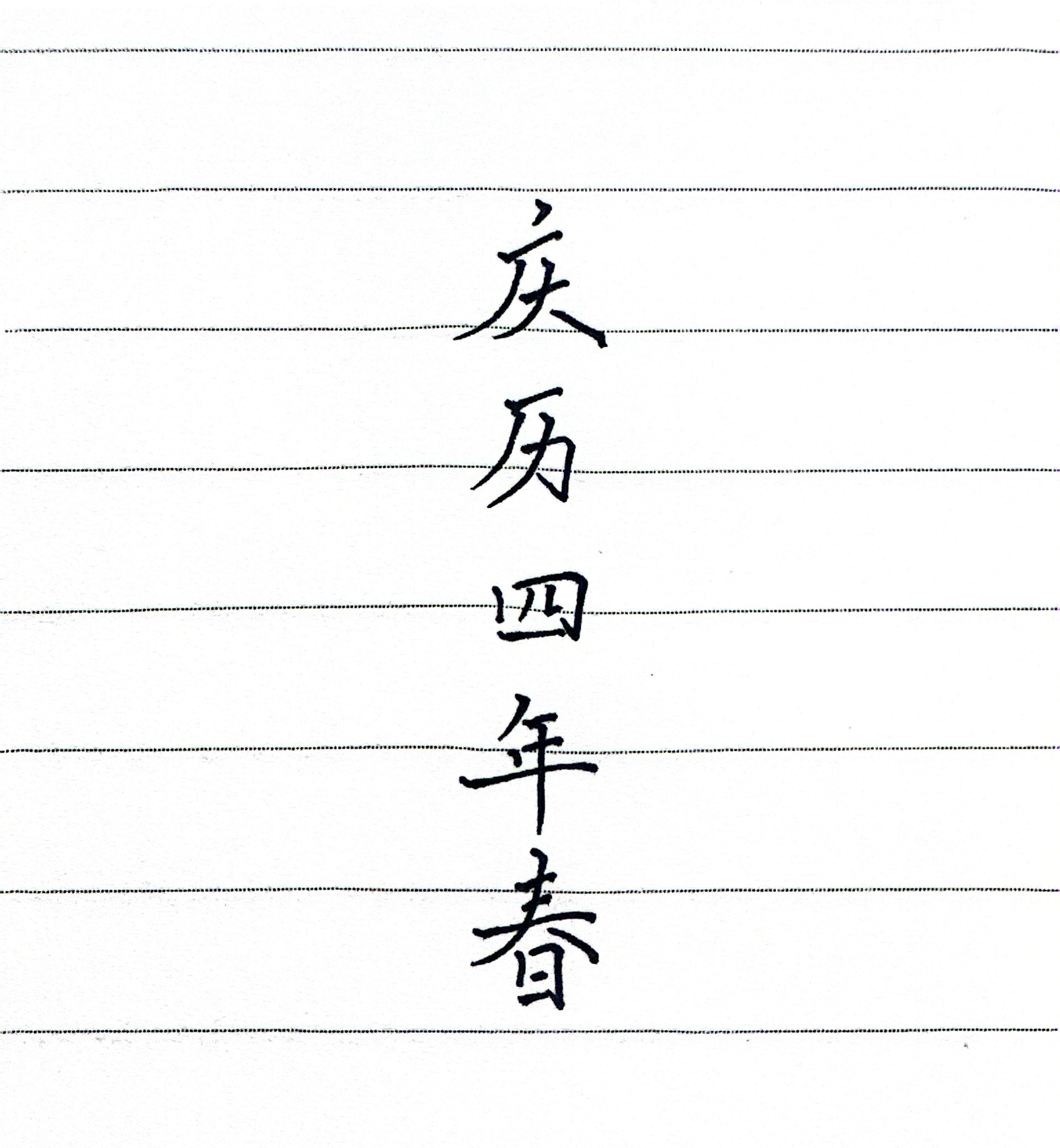三河往事——炼石店(四)北舞渡的班车
微信公众号同名:牵牛福克南
我对沙河最初的记忆,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那是我人生中最早的回忆,更早的幼年,我没有再听他们说过了,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我不是出生在舞阳,而是出生在叶县洪庄杨那个三面环水的冬天的小村子——炼石店。
(一)伍子胥与炼石店
关于炼石店的名字,我小时候问过母亲:是不是女娲补天的时候在这里炼过石头啊?母亲微微一笑点点头,说是的。小学过年回姥姥家的时候,从舅舅那里得知一个叫楚王的人死后尸体在这里晾过一段日子,所以叫晾尸台,后觉“晾尸”不吉利,改称炼石店。我不知道楚王是谁,也不知道他是楚国的王,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名字。于是童年的梦里多了一个场景——那个台子很高,似乎是封神演义里的那个台子,楚王就躺在那里,日晒雨淋,尸体慢慢腐烂,露出白骨,直到最后成为一具骷髅,我没有觉得恐怖,只是觉得可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楚是一个地方,楚王是那里的王,从小比较木讷的我没有过多的好奇心,也没有再去深究他是楚国的哪个王。多年后读史记·伍子胥列传,看到伍子胥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觉得有些熟悉,就查了炼石店的由来,方知,在炼石店的村南的土台上,躺着的就是楚平王,而他是被伍子胥从墓里挖出来鞭尸的。至此,那个错付了多年感情的楚王,突然间死在了我的梦里,伍子胥却成为了我钦佩之人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二)车辙与尿布
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带着我回了姥姥家。30公里的路途,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发了,架子车上铺着麦秸秆,上面垫着草席,又铺了两层被子,母亲坐在车上,怀里抱着我,带着头巾,盖着被子。爷爷把拉车的绳子从头上绕过,跨在肩上,父亲在侧面推着车,伴随着执拗一生,车子缓缓地出发了。村头田间的小道上,车轮碾过煤渣路发出沙沙的声音,架子车后面拖着两道长长的车辙,延伸向远方,模糊在晨雾中,澧河水的咕噜声伴随着晨雾在流淌——那个远方,是家的方向。我想,着当年苏轼和苏辙也经历过这个场景吧,苏洵拉着架子车载着程夫人和两兄弟,走在眉山的小道上,我庆幸父亲和爷爷没有太多的文化,否则我现在的名字好一点可能叫子车、双伦,差一点可能就是轱辘了。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走到姥姥家的时候,已经快到春节了。
那时候春节,姥姥给我准备了很多尿布——冬天的尿布洗了之后要很久才能干,当晚饭后村里人在路边在街口点燃柴火聚在一起闲聊家常与那个闭塞的小村落里的天下事的时候,母亲就抱着我去烤火,姥姥也会拿着我没干的尿布去烤一烤,生怕我第二天没有尿布用。在以后的冬天,看到村里人烤火便会去凑个热闹,话题无非是吐槽日常的生活,小声地聊聊谁翻了谁家的墙,谁上了寡妇的床,怀疑谁偷了谁家的鸡,谁家的羊吃了谁家麦地的苗,随后抛下了几句谴责与同情的话,守寡十几年了,拉扯着俩孩子也没改嫁,不容易,众人纷纷表示同意——那时候村里的人大多是善良的,他们没有什么道德的制高点的批判,有的只是那本家家难念的经,每个人都在念着经,也理解别人家的经,他们都在各自努力地过着各自的日子。
(三)晨雾与死去的伙伴
后来,我会走了,也记事了,要从舞阳去姥姥家,需要坐每天只有一趟的公交,那是一辆风尘仆仆的公交,需要天不亮的时候出门,走到澧河淀,那条通往县城和北舞渡的路上。那是又一个冬日,我站在路旁,望向南方的澧河上,那里晨雾缭绕。
说起晨雾,请允许我跑题到晨雾的回忆里。
关于童年的记忆里,总是冬天和雾交织在一起,或许那是模糊的记忆,晴朗的日子过于欢声笑语,阳光明媚,在温暖的冬阳里晒着太阳,困意袭来,便昏睡过去了,那样的日子很惬意,却难以铭记。
而我更喜欢冬日大雾弥漫的清晨,在雾里奔跑,在雾里,十指划过眼前的朦胧,那缕朦胧在指尖后缭绕回旋后消散又归于白茫茫一片,轻轻捻动双指,只觉半点湿意,半点微凉,似乎抓住过什么,却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雾里奔跑。
在雾里奔跑,仿佛看见童年的玩伴,他转过墙角后没了音讯,我扒在墙角,探出头望去,只看见雾里有人向我招手,我跑了过去,四处张望,我听见他在呼唤,却找不到他,摩托车灯闪烁着,匍匐在地面上,我听见他在呼唤,却看不见他,雾里多了一抹鲜红,他说他和另一个小伙伴要走了。
从此,在冬日的浓雾里,我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整日对着一座新坟喃喃自语,那是一座孤寂的坟,一座不能进祖地的土坟,旁边栽了一株桑树,为他遮风避雨,土坟上没有一株杂草。几年后的春节,我再次见到他的母亲时,黑发已然苍苍了,她时常来我们家的院子,和奶奶一起晒太阳,逢人必说着大儿子的往事,时而欣喜,时而啜泣,祥林嫂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冬天了,那片冬日清晨的雾,却愈发浓了。
(四)照相馆与北舞渡的班车
那是一条通向北舞渡的路,那是离开故乡前,抵达过的舞阳的最北方,听说舞阳的最北是莲花镇,只是我从未到访。那条路继续向北延伸,道旁的白杨树随风哗哗作响,那是我儿时的风铃。风铃在春天响起时,母亲带我走进了道旁的照相馆。那是一家实景照相馆,有亭台静落,假山环绕,桃李芳香,在熬过萧瑟苍凉的冬日后初醒的华北平原上,这里是一隅南方,我在那里留下了一张照片,一张唯一的和母亲的合影——我站在母亲的旁边,她微蹲着,身后是亭子和盛开的桃花。她说,四岁的我已经快要跟她一样高了,快门响起,照片定格,我看着它挂在破旧瓦房的墙壁上的相框里,渐渐被潮气洇湿,边缘泛起了皱纹——玻璃内,虽已是数十年的岁月侵染的昏黄,依旧朱颜不改,相框外,那照片边缘的皱纹,已映在了今人,那满头青丝,又化作了白发几缕?
哪里有什么春天,春天是繁花盛开的季节,儿时的繁花从未盛开过。
我站在十字街口,望向南方的澧河桥上,一辆锈迹斑斑的车从晨雾中缓缓驶来,车头的两块挡风玻璃像眼睛一样注视着迷雾中的世界。吱伴随着最后的吱吱声,车缓缓停下,我和母亲上了车,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不久便经过了照相馆,它在冬日里沉睡着。我醒来的时候,感受到了一股冷气,额头已经贴着哈满水汽的车窗了,呼出的热气继续在车窗上凝结,那层原本的水雾开始汇聚,凝成水珠,慢慢向下滑落,汇聚,流淌,浸湿了我的棉袖,这是一幅与夏天的雨滴击打车窗相反的画面——在冬天,雨落在了玻璃的另一侧,悄无声息。水雾渐渐褪去,蒙蒙的车窗开始清晰了起来,暗绿的麦田给远处光秃秃的白杨树披上了绿叶,窗外的原野在流淌,在徐徐展开。汽车,继续朝北方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