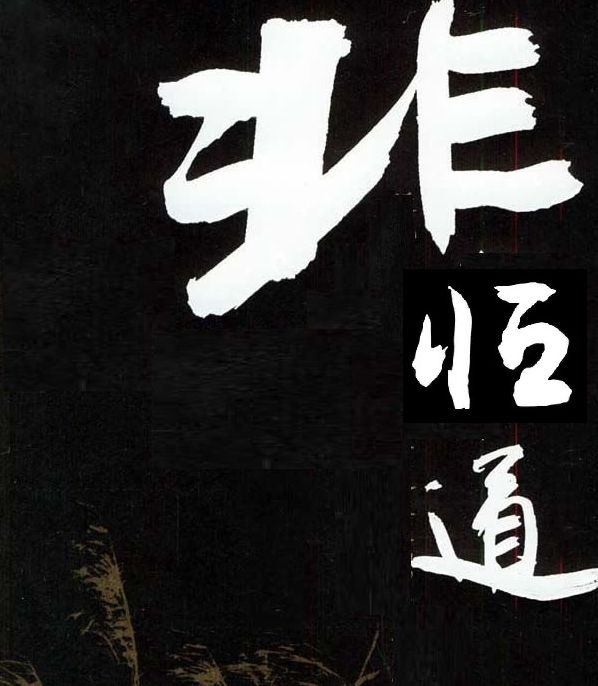吴凤翔刺杀天皇甥
日寇横行华夏地,神州儿女志成城。
不分国共齐行动,斩毙天皇嫡外甥。
话说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开封城的风里总带着些沙尘,混着西大街酒馆飘来的劣质烧酒味,扑在人脸上发涩。山陕甘会馆的朱红大门整日紧闭,门楣上的琉璃瓦在灰蒙蒙的天光下失了色泽,只有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刺刀上的寒光,提醒着路人这里是华北五省特务机关的驻地——吉川贞佐少将的地盘。
吴秉一第一次站在会馆对面的茶摊前时,指尖微微发紧。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个刚从乡下进城找活计的落魄汉子。茶摊主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眼皮耷拉着,对街面上的动静漠不关心,只在添水时瞥了他一眼,那眼神里藏着些麻木的警惕,是乱世里人人都有的自保。
“再来碗茶。”吴秉一低声说,目光却没离开会馆的侧门。那里刚走出个穿绸缎马褂的男人,腆着肚子,走路摇摇晃晃,正是吉川身边的红人权沈斋。吴秉一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是几封大洋,沉甸甸的,硌得胸口发闷。这是牛子龙交代的,说对付权沈斋这样的人,这些东西比什么都管用。
牛子龙是吴秉一在郏县师范的老师,脸上总带着点温和的笑意,讲课时声音不大,却总能让学生们听进去。吴秉一还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说,做人要守本分,更要知大义。那时候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穿着粗布校服,心里装着对革命的懵懂向往,后来经另一位老师王永泉介绍入了党,才明白所谓大义,是要拿命去拼的。
找到权沈斋并不难,他常去西大街的一家窑子。吴秉一在窑子门口等了两个时辰,才等到权沈斋醉醺醺地出来。他上前两步,把布包递过去,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谦卑笑容:“权先生,晚辈吴秉一,有事相求。”
权沈斋眯着醉眼,扫了眼布包上露出的大洋边角,脚步顿住了。他最近正愁着捞点好处,前阵子刘兴周和徐宝光被刺后,吉川对他们这些亲信管得严了些,连平日里的孝敬都少了。“你是谁?找我做什么?”他打了个酒嗝,口气傲慢,却没推开吴秉一的手。
“晚辈是小磨山来的,”吴秉一压低声音,“现在走投无路了,国民政府在通缉我。听说权先生是吉川太君面前的红人,想求您引荐引荐,给我个安身立命的差事。”他故意顿了顿,补充道,“我在山上还有些弟兄,一个营的兵力,只要太君肯收留,我随时能把队伍拉过来。”
权沈斋的眼睛亮了,酒意醒了大半。一个营的兵力,这可是不小的功劳。他把布包塞进怀里,拍了拍吴秉一的肩膀:“这事包在我身上。不过你得拿个投名状,比如队伍的花名册,我也好在太君面前说话。”
吴秉一点点头,心里松了口气。花名册是牛子龙早就伪造好的,纸质泛黄,上面的名字歪歪扭扭,看着像真的山里人的名字。他第二天就把花名册送了过去,权沈斋拿着花名册去见吉川,回来时脸上带着笑:“太君很满意,让我全权负责。不过他最近不大见生人,你先等着。”
等待的日子里,吴秉一住在牛子龙岳父董文学的小院子里。院子很小,墙角堆着些柴火,屋檐下挂着串干辣椒。董文学是个沉默的老头,每天只是做饭、劈柴,很少说话,只有在递饭时会低声问一句:“都还顺利?”吴秉一总是点点头,他知道,这沉默里藏着和他一样的期盼。
三天后,权沈斋风风火火地找来了,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吴老弟,机会来了!太君问你能不能弄到军统刚从重庆弄来的左轮手枪,还让你把队伍带到董章镇验收。”
吴秉一心里清楚,这是吉川在试探他。他装作犹豫了片刻,说:“我试试看,应该能弄到。队伍的事,我这就去安排。”送走权沈斋,他立刻把消息传给了牛子龙。牛子龙的回复很快传来:“验收时带王宝义过去,准备行动。”
王宝义是牛子龙的亲信,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身手利落,枪法准。两人在董章镇顺利通过了验收,那个来验收的日本军官,看他们的眼神像在看两件货物,傲慢又轻蔑。吴秉一低着头,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他知道,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果然,验收完的第二天,权沈斋就来通知他,吉川要召见他。“太君很欣赏你,”权沈斋拍着他的胳膊,“好好表现,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吴秉一跟着权沈斋走进山陕甘会馆时,心跳得厉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激动——那些被吉川杀害的同胞,那些在监狱里牺牲的同志,很快就能瞑目了。
会馆里很安静,只有脚步踩在青石板上的声响。穿过几重院落,来到西厢房前,权沈斋停下脚步:“你进去吧,太君在里面等你。”吴秉一推开门,看到吉川贞佐正坐在一张八仙桌前,穿着少将制服,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桌子旁还坐着几个人,都是日军军官,其中一个正是白天验收的那个。
“吴桑,你的表现很好。”吉川开口,声音干涩,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吴秉一刚要说话,就看到吉川的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王宝义按照计划,以“表现突出的部下”的身份跟了进来。
“太君,这是我的弟兄王宝义,作战很勇猛。”吴秉一介绍道,指尖已经摸到了腰间的手枪。吉川点了点头,刚要开口,吴秉一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了他。门口的卫兵反应过来,大叫一声,刚要端枪,就被王宝义一枪放倒。
屋里顿时乱作一团。一个日军大佐猛地站起来,刚要拔枪,就被吴秉一一枪打在脑袋上,倒了下去。吉川吓得脸色惨白,转身就要跑。吴秉一对准他的后背连开两枪,可枪却卡壳了。吉川愣了一下,脸上露出狂喜的神色,跑得更快了。
吴秉一骂了一句,把卡壳的枪扔在地上,立刻拔出腰间的驳壳枪。这把“二十响盒子炮”是德国造的,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很踏实。他对准吉川的背影,扣动了扳机。枪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二十发子弹一口气打了出去,吉川的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重重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剩下的几个日军军官还想反抗,王宝义端着枪扫了一圈,他们就都倒在了血泊里。吴秉一弯腰,在吉川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一叠文件,塞进怀里。“走!”他低声说。两人并肩走出西厢房,门口的卫兵竟然没听到里面的枪声——街面上的策应人员正在制造喧闹,叫卖声、争吵声混在一起,成了最好的掩护。
走出会馆大门,融入街上的人群,吴秉一才感觉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阳光穿过沙尘,落在他的脸上,带着些微的暖意。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朱红大门的会馆,心里没有丝毫喜悦,只有一种沉重的释然。
后来,开封城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被刺杀了,还有他的参谋长、宪兵队长,一共五个人。《河南民报》首先披露了消息,后来国内外的报纸都报道了,人们都在说,刺杀吉川的是个大无畏的民族英雄。吴秉一的名字,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
再后来,战争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了。吴秉一改回了自己的真名吴凤翔,曾受邀参加开国大典,还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以为,苦日子终于过去了,那些牺牲的同胞,终于可以安息了。
可他没想到,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复杂的历史,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五年,他先后两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监狱里的日子很苦,比他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还要苦。他常常坐在冰冷的牢房里,想起在郏县师范上学的日子,想起牛子龙老师温和的笑容,想起山陕甘会馆里的枪声,心里充满了迷茫。
一九七七年,吴凤翔因为高血压偏瘫,获得了保外就医。他回到了家乡郏县,身体很不好,走路一瘸一拐,说话也有些含糊。村里人大多还记得他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常常有人来看他,给他送点吃的。他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天上的云,一句话也不说,眼神里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一九八〇年的一天,有人从县里来,给了他一份文件,说他被平反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吴凤翔接过文件,手不停地发抖,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他却没察觉。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来,滴在文件上,晕开了墨迹。
两年后,河北军区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一年,他六十九岁,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身手利落、眼神坚定的青年了。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吴凤翔去世了,享年七十岁。下葬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当年和他一起抗日的老战友,有村里的乡亲,还有县里的干部。风里又带着些沙尘,像一九四〇年那个春天一样,只是这一次,没有了枪声,也没有了恐惧。
他的墓碑上,刻着“抗日英雄吴凤翔之墓”几个字,字体工整,在阳光下显得很清晰。来往的人看到这墓碑,总会停下脚步,听旁边的老人讲起当年刺杀吉川贞佐的故事,讲起这个一生坎坷却始终坚守大义的男人。只是他们大多不知道,这个英雄,曾在和平年代里,承受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苦难。
小史公曰:凤翔怀报国之志,临危蹈险诛寇酋,其义烈可比古之刺客。虽蒙冤数载,然丹心不泯,终得昭雪,英雄之名垂于后世,不虚也。
有词《梧桐影》赞叹:
吴凤翔,屠倭贼。逃出虎牢重举旗,人生历史红成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