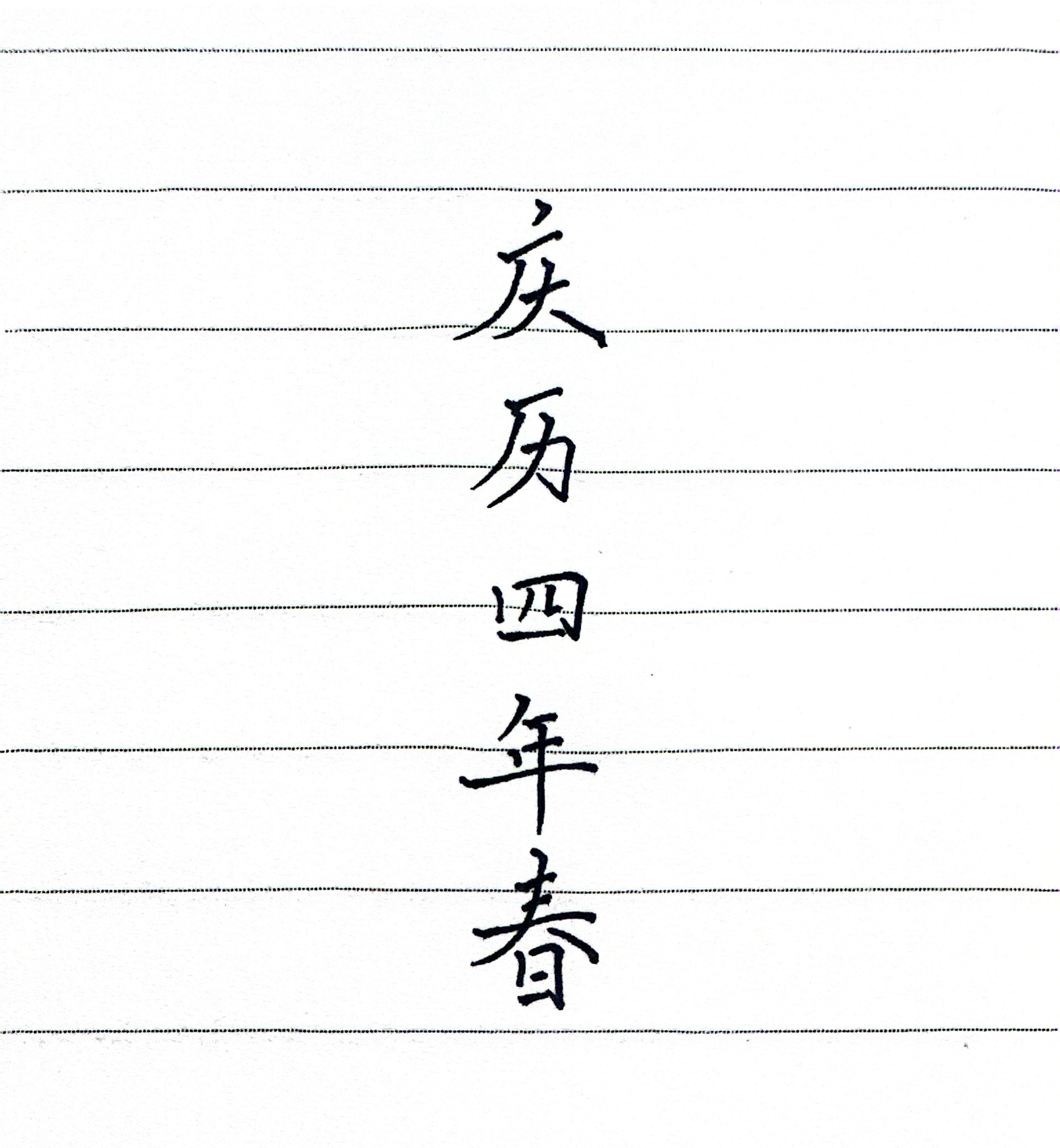星星草(一个关于河南老家的故事)
(一)星星草
我对傻姑的第一记忆,是四岁那年的一个午后,那天的日头可好,却也算不得温暖,家门前的土路上还时不时地刮着西边来的风,我从门口的小石阶上跳下来,见她盘着双腿,坐在西边墙根儿,穿着露着棉絮的花棉袄,黑棉裤在膝盖处破着大洞,屁股下垫着麦秸秆儿。她头发乱蓬蓬地,像披着一堆干草,眼睛微微眯缝着,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随风摇摆着身体,直到注意到她左手黢黑的指尖捏着一株稚嫩的草,才让人想起,这是个春天。
我一眼便认出那是傻姑,听家里人提起过:傻姑的母亲,是她父亲从云南人贩子那里买来的,生了傻姑后就不知去向了,她的父亲,一个沉默得像澧河里的勒缰石的地主老财家的穷孙子,在八八年开春儿——春暖花开却遇上突如其来的倒春寒的时候——咽了气儿。他最放不下的傻女儿——十四岁的小芳,便像断线的风筝,开始在十里八乡的田埂和土路上飘荡了。
又起了一阵风,傻姑又晃了几下,似乎整个巷子里的春天的寒风都要从她身上吹过。
“芳姑,来,坐这儿,门楼底下木有风,暖和。”我朝她招了招手。
她抬头看了看太阳,没有理我。
我顺着墙根儿下的麦秸杆朝她爬了过去:“你拿的是啥啊?芳姑。”
“草。”
“啥草。”
“星星草”
我看着她手里的星星草,不经意间注意到了她干裂黢黑的手背的另一面——她的手心是白的,比我脏兮兮的手要白,捏着星星草的指尖里侧也是白的,跟我姐的手一样,嫩生生的。
“给我看看星星草。”
我伸手去摸,她把手往后一缩,这是我哩。随后笑着指了指我家的土墙根儿……那儿有。
傻姑四岁那年,指着她家土墙下开满的、指甲盖大小的紫色碎花,问她父亲,那是什么,她的死去的老父亲说,那叫“星星草”,贱得很,踩不死。
我顺着四岁芳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只见墙角的土缝里,斜斜地生着几株细碎的小草,还没开花,西风一吹,就晃悠悠地哆嗦着。我并不知道,那一刻,那些在阳光和寒风中艰难存活着的星星草,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终生难拔的悲悯的种子。
(二)糖
我第二次见傻姑时候,已经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了,我坐在屋后的斜坡小路上。
日头落在了西边的树梢上,不多久便斜斜地没入了山墙,暑气也渐渐消散了,收麦的乡亲们陆续从东边的泗上和南边的河坡地里回来了,一辆辆架子车,排着队,吱扭吱扭地缓缓驶来,车前是黝黑的光膀子汗脊梁,肩上挎着攀带,身体向前倾斜出了个45度的迈克尔·杰克逊,车上满载着带杆儿的麦穗,车旁和车后是妇女和半大的孩子,他们也倾斜着身体,并不轻松地迈着反向太空步,一步一步地推着车子向前,他们是杰克逊的舞伴。晚霞里,低着头的金黄的麦穗、车上悬着的装水陶罐、捆麦秆垂下的麻绳,也随着那吱扭吱扭声有节奏地摇摆着,那是MJ的观众和荧光棒,他们一起,在这个一九九一难得的风调雨顺的上半年,在祖祖辈辈生活的豫中平原的舞台上,上演着属于他们的Billie Jean。
我望着他们远去,架子车的终点,是村西头的麦场。在那里,麦穗们会跟老天爷祈祷着好天气,之后要经历几天的日晒,经历反复的石碾子的碾压,被高高扬起在空中——那是他们此生最自由的时刻——让风吹走它的残蜕,被装进麻袋,交足了给公家,剩下的再屯进乡民们各自家的粮仓。要是遇见了暴雨,麦穗们就过不了好年了,到了年底吃饺子的时候,那基本便是萝卜、韭菜的故事了,饺子皮儿也擀得比往年薄一点儿,也会多几声叹息,把夏天的牢骚发到灶王爷那里去,祈求管伙食的灶王爷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了。
“蛋儿,吃雪糕不?”我听到了往后几个夏天都会听到的熟悉的声音。
春洋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是我家东边隔了两户的邻居,是我们四队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大学生,她从去年夏天便开始卖冰糕了,骑着个大杠自行车,坐后面绑了个木箱,外面包着厚厚的隔热棉被。
她停下车,拿了俩雪糕给我,“你跟恁姐一人一个,赶紧吃,过一会儿就化了。”我眯缝着眼对春洋姑笑了笑,她便急匆匆地推着车拐进巷子,进了家,锅碗瓢盆咣咣当当地给下地的父母准备吃的了。
当我的第一根冰棍儿快吃完,不经意间转头向东望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冬天见过的熟悉的身影。天色已经昏沉了,在昏迷前的日头的最后微光中,我看她背着个鱼皮布袋,低着头捡着地上掉落的麦穗,已经装了大半袋了,我想那时候的她是清醒的,因为月亮升起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傻姑并不是天生傻,她也念过村小,和春洋姑是同学,后来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便突然就傻了,她大部分时候是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沉默或癫狂状态,少数时候是清醒的。自她父亲走后,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我朝她走过去,把另一根冰棍儿递给她。她抬起头,迷蒙的眼睛里有一丝诧异。她朝我笑,笑得像水坑里晃荡的月光。她接过了冰棍,嗫嚅着,声音很轻:“要不要糖?”
我脑子里听到“糖”这个词,感到欢喜,向她伸手。她抬手,从那件对襟儿蓝花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颗硬糖,递给了我。她递糖给我的手微微发抖,糖沾了汗,裹着碎麦秸沫儿。我把糖丢在了地上。
“脏,你先吃冰糕,等着我,我去给你拿几颗糖”。
我跑回院子里,拧开门的瞬间,堂屋黑漆漆的,我几乎闻不到煤油味,唯一亮的地方是灶火,母亲跟姐姐在灶火做饭,我偷偷跑回堂屋,拉开了灯,找到糖盒子抓了几颗糖,赶紧把灯拉上。
在灶火的灯光的映照下,大门口有个影子在晃来晃去,我把糖给了影子,影子便回了她的“家”。她的影子是天使的形状。
傻姑是善良的,她愿意把她的糖分给我。我却嫌她的糖脏,给丢弃了。我那时不知道,她的糖对她来说是多么宝贵,甜甜的糖,是她在无边的黑暗与苦难的生活里为数不多的能让她暂时解脱的东西。我以为那是来自天堂的糖,可事实是,那些糖,来自丑陋了人性与罪恶的深渊。
我听闻了,不同形状的罪恶的影子,翻进傻姑家的院墙,或把她拖入玉米地、河坡的杂草丛......影子恢复成人形的时候,会留下几个馒头或几颗糖。
30年后的春节,我曾回到我丢弃那颗裹着麦秸沫儿的糖的地方,那颗糖却再也找不到了。我只能去那个童年的小卖铺,买了一包糖,在一个起雾的冬日,把它们一颗,一颗抛进了冰冷的澧河水里,任它们向东漂去。
(三) 刘老拐
我家后排往东数四户,是刘老拐家,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儿,是个瘸子,小儿麻痹落下的病根儿,走路靠着一副老旧的榆木拐杖和那吱咛吱咛的手摇三轮车。他的家,是两间泥巴和着麦秸秆垒起来的瓦房,多亏他那当过中学教员的爹有先见之明,让他学了修表的手艺,加上两个兄弟的帮衬,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刘老拐家的东边是村里的池塘,池塘边上有一口古井,这里是女人们白天洗衣、洗菜,天黑时洗身子的地方。
刘老拐经常拄个拐杖,拎个蒲团,坐在池塘边。他的眼睛跟着女人们的身子走,谁低头,谁弯腰,谁提水桶,那双眼珠就跟着晃。老太太的乳房像老茄子一样垂着,他也看,甚至比看年轻女人更认真,像在咂摸一颗年少时候没吃到的柿子。晚上看不见了,他便竖起耳朵听,脑海里的画面像西北的信天游的歌声一样悠扬~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
他也早早就盯上了傻姑。
傻姑虽傻,可模样板正,胸前身后,走起路来一晃一扭。我见过刘老拐坐在我家后排大路的石墩子上,一根烟盯着傻姑盯到烟屁股烫了手,才“哎呀”一声丢到脚边,差点烧了人家的麦秸垛。
傻姑在村里飘着,她的炕,是换馍花卷的炕,是换糖的炕,或许我不应该这样说,傻姑没有办法,她无力去反抗那一个个影子粗糙的大手。那些影子们还是要脸的,只敢在深更半夜化成影子。
刘老拐经常拄着拐杖半夜踱到傻姑家门口,那个大门几乎没锁过,傻姑知道,即使锁上,那些影子也会飘过院墙,有一天,日头出来后,锁不见了,之后大门再也没锁过了。
刘老拐看见有影子进去了,几分钟后他便偷偷跟着进去——他怕见到那些影子,那些影子也怕见到他——蹲在傻姑的窗下,侧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有时候听见她笑,笑得呆呆的;有时候是哭,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呜咽又憋屈;还有时候,那声音像在求饶,又像在喘气。
他听得满身燥热,耳朵烫,心里翻江倒海,有时气、有时恨、有时又难受得想撞墙。
等影子偷偷溜走后,有多少次,他想冲进傻姑的屋子,一根拐杖已经拄进了门槛了,可是还是满肚子窝火地退了出去。他要脸,毕竟他得依仗双拐走路,不像那些影子,在黑暗的掩护下,一溜烟就没了。他得要脸,即使他不要脸,他那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他俩兄弟也得要脸。刘老拐退了出去,他把傻姑家大门关上,瘸着腿到了大路上,在夜色里大口抽着旱烟,他抽的脸色发青,眼眶泛红。
他咕哝着:“老子不是畜生,老子是人!”。
傻姑是自己跟刘老拐走的。没有人拉她,也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
她在一个深秋跌倒小产后,躺在床上两天两夜,她笑着,因为她觉得可以去见她的爹爹了。
第三天的早上,傻姑睁开了眼,看到了一束光透过纸糊的窗户上的破洞照了进来。她看见光里,他来了,瘸着腿,拄着拐,左边的拐上挂着一只油纸包的烧鸡,右手拎着一包鸡蛋和红糖。烧鸡还冒着热气,那热气,就像小时候她爹爹从镇上回来,给她带的棉花糖,热腾腾,甜呼呼的。
老拐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他对得起天地良心。
从那天起,傻姑的身子有了归处,老拐的日子也有了光。
她坐在门前吃他的饭,洗他的衣裳。她不再在自己的破屋子里半夜被人扒门窗,而是在老拐的屋里。那被压在软和的褥子上的干净身子,发出一种像唱歌一样的笑声。
老拐抱着她,像抱着一床热炕头上的白棉花:“芳,咱是过日子的人了。”
这是个悲剧,还没有写完
我的微信公众号:牵牛福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