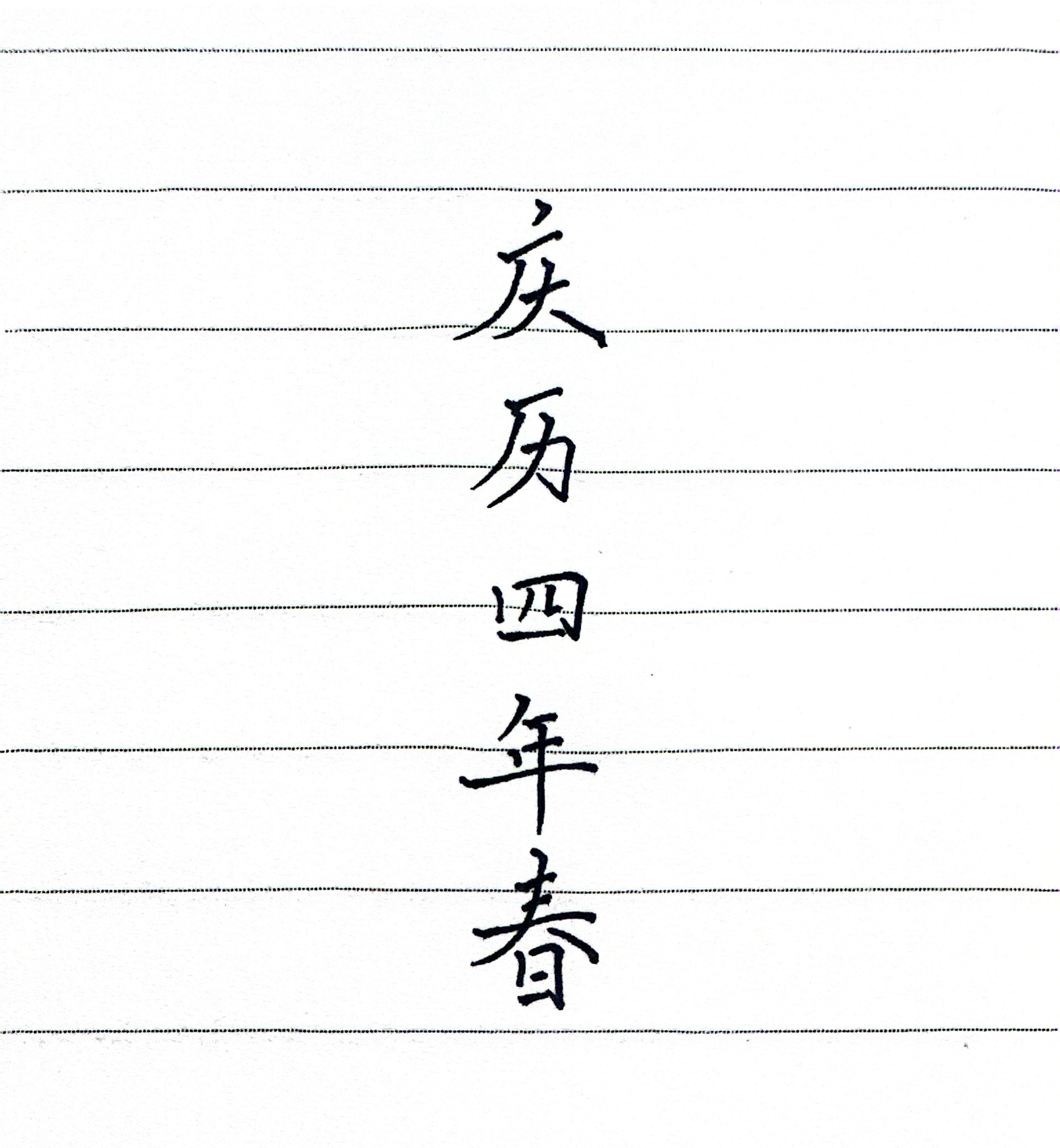从南京到郑州的一棵梧桐树
留园没了,来万维逛逛,几年前的文章了
从局里回来的路上,骑着电车,虽已是傍晚,正午的酷暑仍然残留着尾巴,暖热的风吹在脸上,随之而吹来点,还有风中的梧桐絮。这已是郑州的第五个年头。
第一次来郑州是十年前冬天,在财经政法大学,半个月的日子,目睹了梧桐树从半树枯黄到飘尽,夜里上课很晚,北风很急,满地的叶子。转弯走过那条梧桐树道的时候,风停了,打着旋儿的叶子晃悠了几下,都落在了地上,四周很静,踩上去哗哗直响,那是我第一次在冬天见梧桐树,昏黄的灯,满地的叶子,那条不到百米的路,走了很久很久。
七年前去到南京上学,满城的梧桐让人目不暇接,可是后来生活久了,也便没有了新鲜感,让我再次注意到它们的时候,是冬初的时候,我看到一片叶子在我面前飘落,晃晃悠悠地,落在地上方发现绿色的叶子已经有些许发黄了,抬头看看树上,满树的叶子摇摇欲坠。一个多月后,天寒了,叶子落得多了,时常在西平方的尽头看叶落,摇摇晃晃地,一片,两篇,最喜欢风起,成群的叶子空中乱舞,坠落,扬起,旋转,跳跃。就这样每天看一阵,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我在窗前发呆,很久不见叶子落下来,抬头看看,已是深冬了。之后的两年的冬天,也去过其他地方看梧桐落,也是另一种心境了。
常去研究所后的九华山,那时候没什么钱,山上有五块钱的斋饭,每天中午和师兄弟姐妹穿过研究所的东门,走小径,五分钟便到了玄奘寺,吃了三年斋饭,也拜了三年佛,深秋的时候,银杏叶布满了步道,如果下场雨,没了夏季的蝉鸣,那种意境,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银杏很美,但只能偏安一隅,或深居古禅寺,或伴于帝王陵——南京是梧桐的城市。
在南京第二年的冬天,因为一棵树被砍,朋友告诉我南京不止梧桐,还有一种很像梧桐的树,叫双球悬铃木,仔细看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悬铃木上挂在许多小球球,而梧桐树没有罢了,后来发现,二者都是梧桐树。
那棵被砍的树,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记得晚上回宿舍时候发现土壤所门口的几棵非梧桐树被锯了,只剩光秃秃的枝干。第二天早上经过,发现原来非梧桐树的地方已经被新移植的梧桐树代替。以前我没有注意过他们,直到被砍倒那一刻才发现,原来北京东路的道旁还有这些非梧桐的存在, 那片原来茂密的枝叶全不见了,抬头看到的是有些刺眼的路灯,那昏黄的路灯惨白,惨白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些未被扫去的叶子,风一吹,再一吹。就没有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了。
在南京,做一颗梧桐树才是上等树,那些流亡隐居的非梧桐树,总有一天会被赶出这个城市。
非梧桐的父辈一定教导过他,一棵树的贵贱由他的行为所左右,而不是拘泥于身份的高低,不要以身份的限制作为借口,而虚度自己的树生。
他在被砍倒的一刻也一定心里默念这些话。
愿来生,他是一颗梧桐树。
在记忆里,郑州是个很有坐标感的城市,一直以为这里的路都是以经纬度命名的,直到有一天,那匹老白驹的破马车把我带回了郑州。我期待这里有梧桐树,又不想看到梧桐树。
有一天我发现,这里有很多以树命名的街道,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翠竹街这个名字,与其相伴的是枫杨街,我喜欢这两条街的名字,风扬翠竹沙沙响,只是这里没有风,也没有枫,这里没有阳,也没有杨,翠竹也自是看不到的,之后看到了雪松路,石楠路,冬青街,也没有名字中的树种。在这里,无论何街以何种名字命名,能看到的,只有路旁那一棵棵挂着小球球的树,我认得它,悬铃木——梧桐树。
我抬头望着,路灯突然亮起来,此时已是7点了,这里的路灯的白色的,不是昏黄,这个季节的叶子是绿色的,也不是枯黄,抬头看看路灯下的叶子,绿的,盯久了竟成了黄色,大概是我想起了年少时财经政法大学的梧桐叶吧,微风起,那时的雨,依旧是毛毛细雨吧,看不见,却能感觉到落在脸上,雨中有两位老人在路旁对弈,丝毫不在意这天气。
我在翠竹街前立了很久,看着那一颗颗悬铃木,想起六年前冬天的那些夜晚。那条路我走了数十次,昏黄的路灯下,一片片叶子落了下来,我踩在上面,沙沙作响。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感谢那匹白马。
后来,我到过很多城市,发现每个城市都或多或少种着梧桐树,也有着许多非梧桐树。
…………
这个温热的傍晚,我骑着电动车,梧桐絮扑面而来,经过的街上,还有这其他不知名的树,它们也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只听见风声作响,树枝摇摆,树叶沙沙,已经看不见身边是什么树了,它们一起沉于夜色,等待着明天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