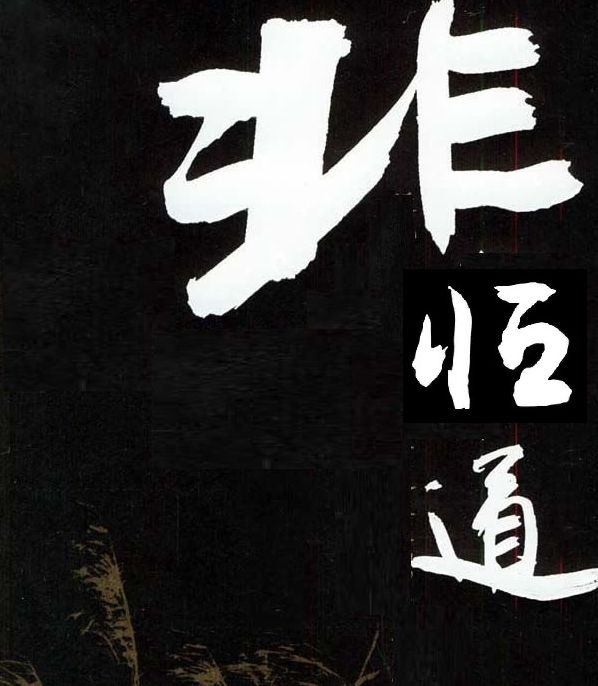王换于二救毕铁华
无心救狗却成狼,狼有犬心救大娘。
救助伤员伤自己,晚年红嫂美名扬。
话说一九三十年代初的沂蒙山,天总是灰蒙蒙的,山脊瘦硬,像穷人裸露的肋骨。王换于——那时她还叫于家媳妇,或者说,于王氏——在山坳里捡到那条狗时,它蜷在乱石间,只剩一丝游气。她把它裹在补丁摞补丁的衣襟里带回了家。狗崽活过来,吃着糠菜团子竟也一天天大了,只是越长越不对劲,眼睛斜吊着,尾巴硬撅撅地垂着。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叼着旱烟袋,远远地瞅一眼,说:“换于啊,这不是狗,是条狼崽子。”
劝的话像秋天的落叶,一层层堆在她脚边。她只是低头喂着那畜生,不说话。终于有一天,压力像山一样沉,她叹了口气,领着那半大的狼上了山。送到深林边,她推了它一把,自己头也不回地往下走。身后传来一声呜咽似的长嗥,她脚步顿了一下,终究没回头。这事,就这么像一粒石子投入深潭,咕咚一声,也就过去了。
沂蒙山区是革命老区,王换于是八路军发展的交通员。有一次,王换于去跑交通,回来的时候是在走不动路了,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忽然,她觉得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抬眼一看是一群狼。她被吓得打了个激灵,本能地拿起石块和木棍和与狼搏斗。眼见寡不敌众,王换于渐渐被狼群包围在中间。狼群撕咬她的衣服,她的手臂和腿上已经被狼咬伤。就在这时,从她身后窜出一条黑影,冲入狼群。经过一番打斗,狼群被驱散。那条黑影却乖乖地趴在王换于的面前——原来这就是王换于早年救的那条小狼。
小狼一直护送王换于回到家里。
却说这位救了小狼又被小狼救了的王换于,她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她家姓王,家境贫寒,常常揭不开锅,家里就用她和村里的富户于家换回了二斤高粱米。她到于家后和于家的儿子成了亲,于是她的名字就变成了“于王氏”,但是大伙儿都管她叫“于家媳妇”。
于家有30亩良田,两片藕塘和一座山。按后来的成分划分,至少是一个富农,甚至可以划为地主。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军扫荡沂蒙山区,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纵机关首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等人率部开发沂蒙山根据地,住进了东辛庄。部队把指挥部和首长安排在于家。除了王换于和她家里的人政治可靠,更是因为于家比较富裕,有地方住得开,有粮食供得起。
朱瑞的夫人陈若克认为“于王氏”是封建时代对妇女的不尊重,于是就给她取名王换于。
王换于入党以后,还把丈夫和儿子也带进了这支队伍,心里那点模糊的念想,仿佛有了清晰的形状。
一九四一年冬天,鬼子拉网扫荡,风声紧得能勒死人。一天下午,邻村一个小伙用独轮车吱呀呀推来一个人,直接放到她家炕上。那人浑身是伤,衣服和皮肉黏连在一起,散发着焦糊与血腥混合的怪味。小伙喘着粗气说:“大娘,这是《大众日报》的同志,从鬼子那儿抢回来的……那边交代,要是救不活,就……就找个地方埋了吧。”
王换于凑近,用手探了探那人的鼻息,极微弱,一丝游气,和她当年捡到那小狼时一样。这一丝气就是一丝命。她没说话,让闺女冲了碗珍藏的红糖水,和老伴一起,用筷子头撬开那人紧咬的牙关,把糖水一滴一滴溜进去。那人的喉咙动了一下,眼皮颤了颤,睁开一条缝。她认出来了,是常来送报纸的小毕,毕铁华。
为治那身烙伤,她什么偏方都试了。熬獾油,烧自己的头发拌进去,抹上去不见好;又漫山遍野挖老鼠洞,捉来还没睁眼的小老鼠泡芝麻油,制成“老鼠油”,这回见了效。伤口慢慢收敛,结起深褐色的痂。她每天用艾草水给他擦身,两个多月,毕铁华能从炕上坐起来了。临走那天,这个被烙铁烙也没掉泪的汉子,扑通跪在她面前,额头抵着冰凉的土地,哽着喊了一声:“娘!”
这一声,把她的心和什么更辽阔的东西拴在了一起。
队伍转移时,她看到首长们的孩子瘦得像小猴,心里揪着。她去找徐司令,说这样不行,孩子得分散开养。于是,她家成了“地下托儿所”,这个送来,那个接走,炕上、院里,总响着别人的孩子的啼哭和嬉闹。她自己的孙子有时饿得直哭,儿媳忍不住抱怨,她抱着别人的孩子哄睡,低声说:“咱的孩子没了还能生,这些同志的孩子要是没了,就真没了。”
也有得罪人的时候。副区长龚报思想把孩子送来,她没应承。不是心硬,是实在塞不下了。就为这,名字从党员册子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像用橡皮擦掉铅笔字。
世道又变了几变。
解放后,因为王换于和他的家人的革命经历没有记录,所以她们一家都只能是普通农民。她找到镇上、县上,都没有结果。王换于说自己的革命经历是有很多大首长可以作证的,还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陈若克,我的名字就是我入党的时候她帮我起的。
负责这事的人正是公报私仇的龚报思,他坐在桌子后面,手指敲着光秃秃的桌面:“陈若克?那你就让她写个证明,盖上她单位的公章。”
“陈若克同志牺牲了,你不知道?”她盯着他。
龚报思摊开手,脸上是一种混合着假装遗憾和公事公办的神情:“那我就没办法了。你不是最讲原则吗?找到证明人,手续齐全,我就办。”
王换于给陈若克的丈夫、那位大首长朱瑞写信。信纸是赊来的,字是一个识字先生代笔的,她郑重地按了手印。一封,两封……信寄出去,像扔进无底洞,连个回声都没有。
日子坍缩回最原始的形态:挣工分,吃饭,活着。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多,她的两个儿子也没撑过去。到了那十年,成分变成了“地主婆”——她嫁的于家,当年确有几十亩田。批斗,游街,唾沫星子溅到脸上。她低着头,心里一遍遍念着那些名字:陈若克,朱瑞,徐向前……可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自身难保,成了“走资派”。没人能证明她是谁。
也有被人找上门要证明的时候。那天,两个表情严肃的人走进她低矮的泥屋,说是来调查毕铁华。“他有没有叛变?”问题直戳戳的,像刀子。
她的话头一下子被扯到好多年前,那个浑身焦糊的年轻人,那碗红糖水,那些吱吱叫的小老鼠。“……他怎么会叛变?抬来的时候都说只剩一口气了……”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为那时的惨状,也为此刻的惶惑。
那两人不耐烦地打断她,递过几张写满字的纸:“在这签字,证明他没叛变。”
她不识字,只认得“毕铁华”几个字是没错的。纸上的其他字像一堆乱爬的蚂蚁。她犹豫着。
“就在这空白处写‘毕铁华没有叛变’。”其中一人指着一个地方。
她蘸了蘸笔,手有些抖,慢慢地,描下那七个字。写完,心里空落落的,不知自己究竟担保了什么,又能否担得起。
风波过去,没人再来批斗她,但也无人提起她的过去。老屋更破了,炕席遮不住土坯,一架旧纺车吱呀呀转着,纺着似乎没有尽头的穷苦。她听说,那些老首长都“复出”了,报纸上能看到名字。她等啊等,院门口的土路,安静得只长荒草。
她最挂念的还是毕铁华。托人打听过,没有音信。夜里常做梦,梦见他又血淋林地站在面前,喊娘。惊醒后,对着黑漆漆的屋顶喃喃:“铁华……怕是也不在了吧。”
一九八二年秋,天高了些。她坐在院里择野菜,老眼昏花。一个身影在门口迟疑了半晌,才迈进来。是个老人,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却满面风尘。那人盯着她看,看着看着,浑身开始发抖,突然踉跄几步,扑通跪倒在泥地上,未语泪先流:
“娘——您不孝的儿子……来看您啦!”
她吓了一跳,眯起眼仔细辨认。皱纹、白发、陌生的苍老……但那双眼睛里的光,还有那轮廓……
“你是……?”
“娘,我是铁华!毕铁华啊!”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她颤巍巍伸出手,想碰又不敢碰。“不像……不像……”可手还是落在他肩上。
毕铁华猛地解开衣扣,扯开衬衫:“娘,您看!您摸摸!”
她枯瘦的手探进去,触到的不是温热的皮肤,而是凹凸起伏、坚硬而狰狞的疤痕,一片连着一片,烙在胸膛,烙在背上。是她当年用老鼠油一遍遍涂抹过的地方。
手停住了,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半晌,一声压抑太久的呜咽从她胸腔里挣脱出来:
“是铁华……是俺的铁华呀!”
“娘啊!——”毕铁华一头扎进她怀里,嚎啕大哭。
进了屋,毕铁华愣住了。破炕,烂被,旧纺车,泥盆里几个冰冷的菜团子。他环顾四周,嘴唇哆嗦着:“娘……您不是……老革命吗?怎么……怎么还这样啊?”
她垂下眼皮,用衣角擦擦炕沿,让他坐。“他们说,没人证明……陈科长、朱政委,都不在了……我找谁去呢?”
“我呀!娘,您找我呀!”毕铁华握紧她干柴般的手,眼泪又涌出来,“您当年救了我两次命,一次是从鬼子手里,一次……是从那些人手里。”他想起了那场调查,那份关键的、字迹歪扭的证明。
“你那时候……自身都难保。”她摇摇头,想起那两个人冰冷的脸。
毕铁华没再多说,只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他在她破旧的老屋里住了几天,然后开始奔波。县里,省里,北京……他带着一身伤疤和不容置疑的证词。
毕铁华四处奔走,终于恢复了王换于的革命者身份。
一九八六年农历五月初七是王换于九秩晋八大寿。那天,院子里忽然热闹起来,来了好多车,好多人,有当年的“小战士”,如今也白了头,有各级的干部。祝寿的声音,敬酒的声音,照相机的闪光,混成一片陌生的喧哗。她坐在主位,穿着簇新的衣服,有些茫然地笑着,像个局外人。
寿宴过后,人群散去,老屋重归寂静。她让人换下新衣,依旧坐在炕沿,纺车就在手边。一切似乎不同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只有那匹很久以前放归山林的狼,偶尔还会潜入她的梦里,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中望着她,安静而坚定,像某个永恒的、未被证明的誓言。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王换于在百有一岁时,告别老屋,与世长辞。
有词《梧桐影》赞叹:
红嫂情,无人记。畴昔故人来不来?教人敬佩教人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