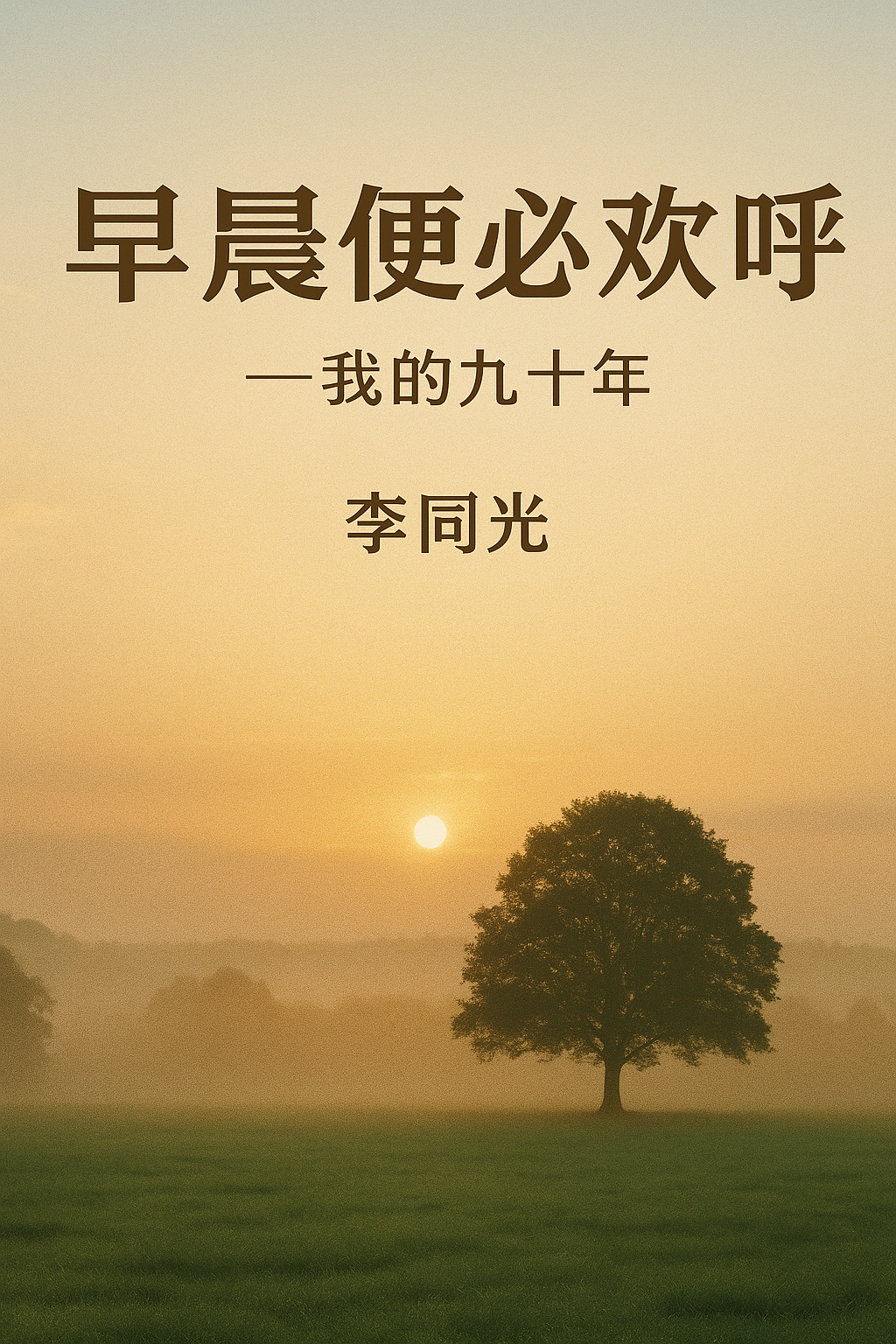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七章
第三部:
将残的灯火
第七章
父亲的圣经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
这是一部用繁体字竖排版的《新旧约全书》(左图)。它原有的枣红色硬漆封面已经皲裂,周边还有多处磨损。但是,在我所有十二部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中,我对这部外表陈旧的圣经,却怀有最特殊、最深切的感情,因为这是先父生前最后读过的圣经。虽然饱经风霜,这部圣经不但是带领我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还见证了始自1949年5月以来,我们一家在中共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1948年春,先父因多年的胃溃疡,在南京鼓楼医院做胃大部切除术。半年后,他突发上消化道梗阻,乃到上海枫林桥中山医院第二次手术。院长沈克非教授[1]亲自主刀。
手术那天,母亲在等候室焦急地等候消息。但仅仅等了三十分钟,沈院长就走出手术室。他十分沉重地对母亲说:“胃癌已广泛扩散,没有办法切除”。父亲在十天后出院。这部圣经就是不久之后,他自己去上海圣经公会购买的。
1948年12月,中共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导致上海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人们想方设法,要逃出这个曾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繁华城市。就在那个混乱时刻,沈院长特地到我们住处,看望病势沉重的父亲。
1949年1月25日,礼拜二,天父接走了时年49岁的父亲。母亲那年39岁,我14岁,还有弟弟妹妹五人,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
整整四个月后,即1949年5月25日,中共“解放”了上海。
我继承了父亲的这部圣经。1950年,我随母亲在上海虹口灵粮堂聚会;1951年,我17岁时在灵粮堂受浸;1952年,我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医学院(上图:上海医学院大门)。
进入上医的第一天,我大为惊喜地发现,在学生饭厅墙上,贴着一张基督徒聚会的通知,聚会地点就在上医主楼顶上的“东亭”。我充满喜乐地按时前往,参加了有20多位弟兄姊妹的聚会。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有家在上海的,也有从外地来的,而且有不同的教会背景,但是天父的大爱使我们互相融合为“一家人”。7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张1953年摄于“东亭”的上医基督徒的集体合影
(下图,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站立者为本书作者)。
可是1955年夏,“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我们的学生基督徒团契也被迫停止活动。
那些年间,每逢周六我回家,无论走在路上或在公交车上,我总喜欢腋下夹着父亲读过的这部圣经,而且将枣红色硬漆封面向外,我巴不得人们看见《新旧约全书》几个大字,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上医不久易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上一医),后来又改名为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1955年秋,我从上一医外科专修科毕业。面对毕业后的“全国统一分配”,我不知如何走前面的路,但我深知“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箴言》20:24);我应当“一无挂虑”,“信靠顺服”,因为我“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诗篇》31:15)。
有一首诗歌常使我热泪滚滚:“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你的喜欢。”
我顺从天父的带领,先到河南郑州,后来又去位于汲县(现名卫辉市)的新乡专区医学院(现名新乡医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远离亲人和繁华的都市上海,虽然我对外部环境有一些新鲜感,但怀念故乡、思念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心情与日俱增。
我无比珍爱父亲留给我的这部圣经,因为先父归天11年(1949-1960)以来,它是我们家中唯一尚存的遗物。我特别爱读父亲生前用红笔在我继承的这部圣经上所划的经文:“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以赛亚书》30:29)。每次读到这里,我内心里就会涌出一种特别平安的感觉,因为我深信耶和华神也是我的“磐石”和“依靠”(诗篇18:2)。
今天,我静坐桌前,仔细回顾自己1951年受浸以后走过的脚步,深切感受到父亲留下的这部圣经尤似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我的茫茫思绪和不平凡的经历中。因为我绝未料到,在我被分配到河南工作后的二十余年间,我经历了两次令我魂飞魄散的政治运动。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全国大约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教师、作家、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他们因为响应毛泽东要广大人群给中共“提意见”的号召,并得到“言者无罪”的许诺,结果掉进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深渊而不能自拔。
1958年春,我涉世未深,被新乡专区医学院几个中共党员的甜言蜜语打动,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向党交心”运动。为了摆脱自己出身“剥削阶级”的烙印和桎梏,我向党交出“资产阶级黑心”,要“脱胎换骨”,跟党一条心,认真改造自己。可是到1958年深秋,风云突变,我这半年前“向党交心”的模范人物,却成为第二次反右中“借交心向党猖狂进攻”,是一个“自动跳出来的阶级敌人”!
1959年1月,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把我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的处分是留校“监督改造”,每月工资由人民币57元降为30元。
1960年6月,我突然又被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一直斗到8月!在批斗会上,学院保卫科长拍桌瞪眼向我嘶吼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没有信仰自由。但你还信基督教,竟然还把你的圣经放在桌子上,这就是抗拒改造。”会后,他责令我必须亲自交出这部圣经。当我亲手捧着这部父亲读过的圣经,听命送交保卫科时,心里悲痛至极,似被利刃刺透。
1960年9月28日上午,我在全校职工大会上被戴上手铐,押进汲县看守所;我的罪名是“坚持唯心主义立场,抗拒改造”。三周后,我进入河南省第二监狱。1962年5月,又被转到河南焦作劳教农场。
1962年7月,我在河南焦作劳教农场突然被召回在汲县的豫北医专(即原来的新乡专区医学院)。当年那个骄横霸道、颐指气使的保卫科长已从豫北医专调离。在全校职工及学生大会上,校党委领导为我平反,向我道歉。两年前(1960年),我被勒令含着眼泪上交的那本父亲的圣经,也终于原璧归赵,完好无损地退还我手中。重见这部圣经,我心头无限震动,眼泪夺眶而出。我向神说:“我的神啊,我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比万有更大!”
1962-1965年间,天父带领我过了几年没有提心吊胆的安稳日子。可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5:7)。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敏感地觉得又要大难临头,但自己唯一能做的应变措施,是将这部曾经劫后余生的圣经用挂号邮件寄给母亲。我以为上海是大城市,圣经留在上海总比留在河南要安全一些。
果然,我又成了众矢之的。我头上的新“帽子”是“劳改释放犯”、“牛鬼蛇神”、“刘少奇平反的右派分子”等等。作为被审查的“重点对象”,我又被群众“批斗”,天天要“交代”问题。直到1971年春节前一天,对我审查的最后结论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驻校“军宣队”和“工宣队”准我假14天回上海探亲。
久别多年(1966-1971)的母亲与弟弟妹妹们看见我能回来过春节,十分欣喜,因为这是父神所赐的厚恩。母亲告诉了我这部圣经在上海家中的奇妙经历,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见证。
时光回到五年前,正当1966年文革翻天覆地的日子,附近一个化工厂的“革命造反派”来抄家;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来个戴着红袖章的大汉抄了三四个小时,他们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地抄走了我妹妹的二百多册再也买不到的原版钢琴谱,以及妹妹的一些首饰;可是,来抄家的这些凶神恶煞般人却“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创世记》19:11),居然无人发现清清楚楚摆在茶几上的这部圣经!妹妹的精装琴谱被送到造纸厂当作废纸回炉,这部圣经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在身处不可名状的中共政治高压下,我被黑暗围困,甚至失去继续做人的信心,在灰心绝望中,我只想如何了断生命。但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因为救主耶稣“爱我到底”(《约翰福音》13:1)。人生多有困难,天父有更多恩典。
自从1949年父亲回天家后,至今(2025)已历时76个年头,天父大能的手保护我历经“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如火一般的试炼。父亲留下的这部“新旧约全书”,虽然历尽沧桑,但至今在我身边,永不分离。因为“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89)。
[1] 沈克非(1898年3月2日—1972年10月9日),中国外科学先驱者之一、医学教育家。1924年获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医学博士学位。详见《维基百科》(Wikipedia,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