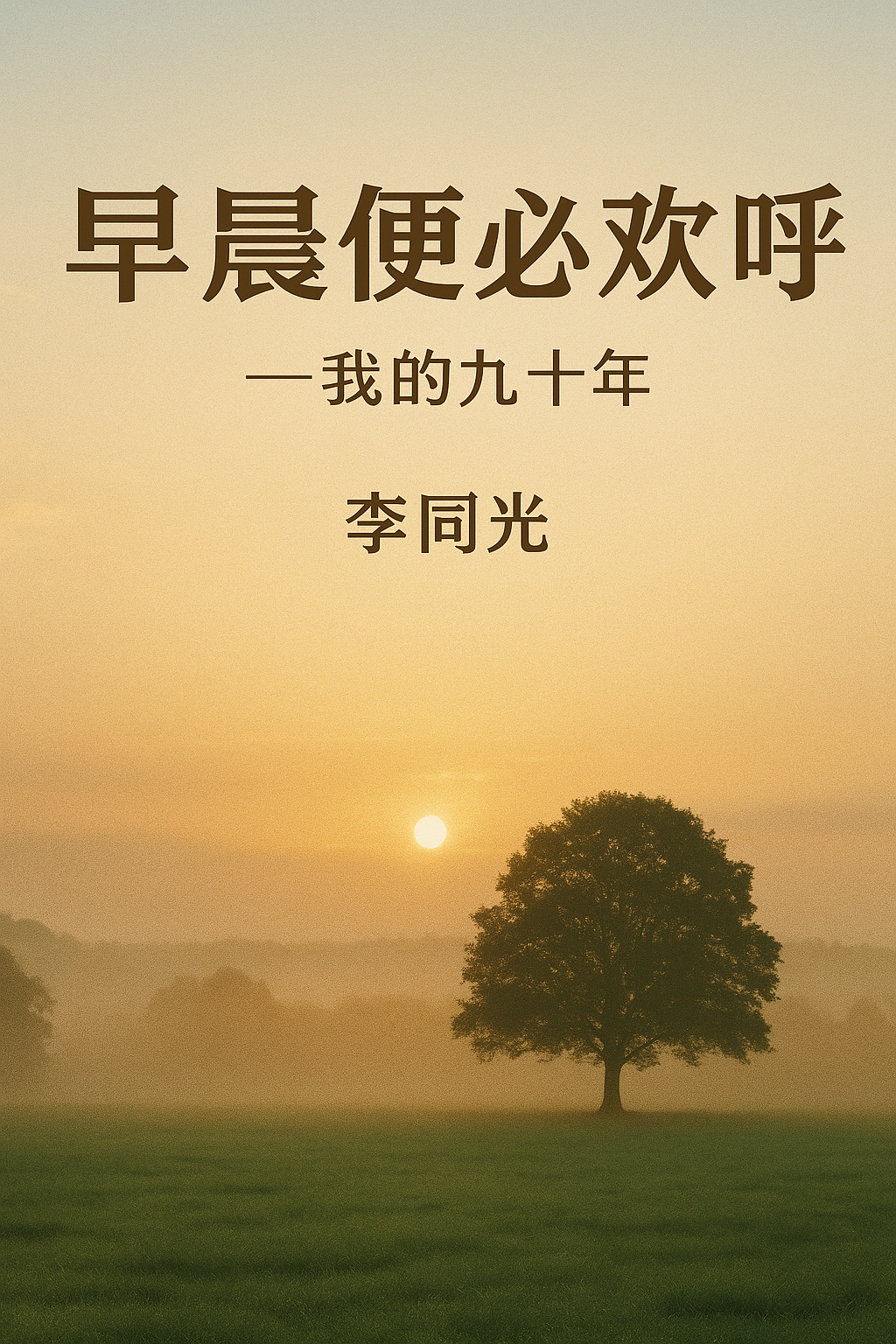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四章
第四章
我的儿子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4:3)
因为晚婚,佑安怀李浩时已近35岁。她在上海仁济医院妇产科做产前检查时,医师发现她的骨盆狭窄,因此分娩时很可能要做剖腹产。我当时身在豫北医专,教学任务第一,高龄初产的妻子快要临盆时,我无法回上海。好在佑安的大姐是仁济医院儿科医师,她要我放心,届时她会安排一切的。
1975年4月15日,那天是礼拜二,儿子平安出世。我的母亲和妹妹万分欣喜,结伴到仁济医院探望佑安和这位刚落地的李家长孙。奶奶给他取名叫“浩”;因为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书》1:19)。天上的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祈求,李浩是顺产,佑安也并未因骨盆狭窄而做剖腹产手术。
三个月以后,学校放暑假,我立即回上海探亲。暑假瞬间过去,我这近41岁的丈夫和父亲却仍然不会服侍产后的妻子和刚刚四个月大的儿子,迷离混沌中,又要匆匆北上河南。
感谢天上的父,佑安母子住在我母亲的家里,有我妹妹和弟弟们的爱心帮助,我不用为产妇和婴儿担忧什么。
那时,我的月薪是65元;佑安更少,只有35元。儿子的费用以及寒暑假我往返上海河南的火车票更是一笔大帐。我们每个月的开销好像总缺百元之数。所幸孩子外婆常在经济和物质上帮助我们。
佑安是一个能干的好管家;从不叫“苦”,也不让我有后顾之忧,我们连“吃”带“穿”,她都一手包办。全家三人的日子,虽然“比上不足”,却也“比下有余”。
假期一过,我回河南,佑安就带孩子回娘家住。为此,我们热切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谈何容易,单凭佑安母子二人的上海户口,在十分“房荒”的上海市,怎能奢望比“老虎”更“厉害”的房管局,会分房给这没有丝毫“人际”关系的三口之家呢?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记》18:14)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埃及记》33:19)。
1977年夏,上海市静安区房管局居然在杨浦区凤凰新村给佑安母子分配了一个14.8平米的房间;虽然是在三层楼上,且和另一个六口之家合住一个单元,但是,“煤气”、“卫”(抽水马桶)俱全,而且房间向南,“阳光充足”,依然引人羡慕。
亲人们帮我们粉刷墙壁,油漆地板。佑安的弟弟正好从新疆回上海探亲;为我们的乔迁之喜,他从好友那里借了辆大卡车,帮我们迁入新居。那天,佑安十分欣喜,因为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安置好新家以后,我们常请亲人们来吃饭。这“家”虽小,却充满家的温馨。虽然过道对面的邻居,渐渐“扩张”他们的“疆界”,占据了走廊及卫生间两家共用的“巴掌”地,我们总以“和”为“贵”,从不争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这新居的美中不足之处,是住房墙壁薄了一点。以致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寒冬寡晴,室内也会结冰。李浩两只小胖手红彤彤的,他冻得直哭。佑安赶紧冲了两瓶热水,给父亲和儿子每人一瓶暖手,她自己却在刺骨冷水中洗衣服,洗床单。床单晾在窗外衣架上,很快就冻成冰片。半个月的寒假,如流水般过去,板凳还未坐热,我又要走了。
佑安上班,单程要走40分钟。她抱着儿子,还要带上奶瓶、尿布等,风里去,雨里来。每逢冬天,她总是把小李浩裹得严严实实,圆滚滚的像一个“泰迪熊”。这“泰迪熊”在斗篷里喜欢后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抱着他,格外费劲吃力。多谢一位住在附近的女老师,常来帮佑安一把;而我只身在千里之外,一点不能尽上做父亲的责任。
又过了一年,大喜事一桩。佑安像中了头彩似的,分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证。这辆珍贵的凤凰牌自行车耗去她半年的工资。可是从此以后,李浩可以坐在母亲的自行车上去托儿所了,每次下班回来,母亲要把这辆车扛上三楼,以免小偷光临。有一次雨后,泥路积水,佑安连人带车翻入泥浆,母子二人成了“落汤鸡”!
还有一次,佑安腹泻、发烧,病在床上。小李浩哭着叫喊闭着双目的母亲:“妈妈啊!侬不能死啊!侬要死了,我就是孤儿啦……呜……”后来佑安告诉我,那一年,李浩刚七岁,才上一年级。听她说起此事,我内心倍感伤痛。
有时,我也能十分幸运地在暑假前回上海。有了这辆“凤凰”,每晨李浩坐在“前座”,佑安坐“后座”。我把儿子先送到托儿所,再送佑安到打虎山路小学上班,自己从杨浦区骑这辆“凤凰”,到静安区胶州路中华医学会图书馆查文献,十分潇洒。
小李浩没有什么玩具。他最爱的就是脚踏车和汽车。他常把锅盖当作汽车方向盘,可以独自玩上两个钟头。有一次,我们带他去南京路中百一店,花了五块钱为他买了一把他一直想要的“带脚的机关枪”。我在付钱,佑安告诉我他在我身后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
我们去外滩,看见黄浦江中成串的大小驳船和机帆船,小李浩说“船父亲和船母亲带一家们去散步了”。在黄浦江边,当他看见我和佑安新婚后去青岛乘坐的“工农兵五号”,他问我们:“为啥你们不等等我,让我和你们一同去坐这大轮船呢?”
每次到奶奶家,我的妹妹和弟弟们都拿李浩当宝贝,总要留他住上几天。每逢周日,佑安都会带他到武定路看望外公外婆。
寒暑假到了,他最开心的事就是能和母亲一同到上海北站接父亲,因为接到我后,可以一起坐汽车回家。但要车的人多,不一定每次都能叫到出租车。
当我所乘的列车徐徐驶入上海北站,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看见站台上等候着我的妻子和儿子,心里满溢着无法形容的快乐。可是等到假日过完,我又要和佑安李浩母子分别,心头又涌出不尽的伤感。并且我额上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无形印记会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预料是否还有“厄运”在等着我。
佑安后来告诉我,每次我回河南后,儿子总会说:“我不开心,父亲走了,没有人带我去杨浦公园骑脚踏车;也没有人买橘子水给我喝”。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他那天真活泼的“跑跳步”,我只看见过一次;他那清脆悦耳的童声歌唱,我一生中也只听见过一次。
1980年夏,我只身来到美国。夫妻父子,一别就是五个年头。在中国国内时,我每年除了寒暑假,都会经历亲人分离的痛苦;来到美国,又是彼此漫长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