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叩击一代人灵魂之作 冯知明

1.诺贝尔文学奖待遇
我注意到,2024年以来,各种媒体和平台集中推送莫言先生的《晚熟的人》出版信息,作者与两位名家亲自站台,在纸质出版物式微的当下,出版业像打了一剂强心针那样,令人一时为之侧目。我注意到媒体推波助澜大势渲染的是,这是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沉寂多年之后的新作。有些评论称诺贝尔文学奖为“死吻”,作家一旦获奖,便如古贤那样只能“述而不作”,其实是“高光之后,盛名之下,江郎才尽”了,然而只有莫言先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本人拖至今日,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一口气拜读完毕,见到书后附有“本书作品创作年表”,最早的《澡堂与红床》是在2011年创作的,最近创作也是2020年3月份。第一次印制为2020年8月份,看来媒体除哗众取宠外,总能找到刁钻的角度,以求吸引观众。
这其实是一部由12部中短篇构成的一个作品集,这部作品集通过不同人物和故事,描绘了高密东北乡在几十年时代浪潮下和社会变迁中的众生相(《贼指花》例外)。“晚熟”是什么主旨,它是一个中性词,或是不管生活多么坎坷而能保持着一颗善良初心(有奶腥味,眼神热烈的女子);或是吃亏上当大彻大悟之后,变得精于算计的蒋二;或虚幻于怀才不遇中难以“晚熟”的表弟宁赛叶;以及“坏人变老”的“高参”覃桂英。这样简单的解读,让作者笔下的人物符号化是肤浅和不确切的,对于读完之后有话要说的人,大抵要作简单的归纳。
二十世纪80年代我曾接触过大量的当代文学,类似把作家当成明星一样的追星行为。渐渐地,受日常琐碎之事所累,本人同样接近“晚熟”,便不再如饥似渴地拜读一些当代成名之作。窃以为,我们现当代作家,受西方经典文学的影响甚重,如要追溯源头和深度,不如直接去读那些西式百年经典,如果要了解文学的高度,仔细研读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即可。
高行健先生和莫言先生是立在世界文学之巅的华语作家,他们描写的环境和人物,皆是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的“映射体”,更有熟悉之感,我却迟迟不曾涉及。早年看过莫言先生在杂志上发表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而高行键先生的大作一直与我遥不可及。这里有我的“源头说”,更惧拜读后自己尝试创作时被潜移默化受其影响,以至不由自主“抄袭”创意或“借鉴”式写作。这半年,由“抒情的森林”发起的作家“抄袭事件”,对当代写作者产生的巨大震荡,不会随风而逝的,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这个国度面对两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莫言先生长久处在排山倒海的谩骂和围攻之中,某作家评价他是“头戴皇冠,身带枷锁”真是一语中的;而高行键先生也许是法籍华裔身份,则完全被漠然、被忽视,让人们觉得他不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两个极端一个被冷冻一个棒杀,网络上定期冒出话题,一些“斗士”披甲上阵,好不豪迈,加上各种论战,忍不住好奇,觉得应该找来《灵山》,读读《生死疲劳》,以便让自己多点鉴别能力,不至于被“弄潮儿”牵着鼻子走。
原以为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者不受待见,近来发现,也非完全是“中国现象”,在奥地利待了半年多,同时注意到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2004年的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另一位是2019年的彼得·汉德克。耶利内克认为奥地利反思二战纳粹战争罪行不够,而汉德克与国内政治观念相悖,使他们受到冷落,我在维也纳想找他们的哪怕一个活动场所,而这座留下他们气息的城市,被誉为音乐圣城和文化之都,则不见踪迹,更说不上开辟纪念地了。作为一名作家,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特质,有此,自然为世俗和权贵所不容。
只是西方人的这种漠然,要比敝国豢养的冷兵器时代的“剑客”要高明,显得有教养得多。
闲发一些议论,还是应该回到拜读《晚熟的人》本身。
2.跺手者的无惧,绝对反击者无畏经典

我在荒芜的幼年,曾仔细观察过打铁匠,莫言先生如同工笔画般的描写,让我回想过记忆中的打铁匠。年少时曾去我父亲的乡镇企业上班,他的工厂有铁业车间,打造农具、菜刀、镰刀等乡间的日常用品,我央求过铁匠师傅,给我打造一把小菜刀,那菜刀只有家用菜刀一半大小,轻便袖珍型的,好看,用起来颇为锋利。与一位铁业车间的铁匠师傅祁中州交上了朋友,我如今还记得他从前的样子,两道茂密粗壮的卧蚕浓眉和一双明亮的眼睛,生长在湖区则是个旱鸭子,有一次我们4人在一座涵闸桥边晒太阳,另一位朋友突然把他推下水,他真像个秤砣那样往河底沉,我们慌忙把他救了上来。记得他不曾恼怒,还说:“你们试了就晓得了吧。”
他是个优秀的打铁匠,每天上班时会把一块铁与徒弟反复锻造成钢,再用火钳剪成长方形的块状,打刀器时,便会包在铁器的刃面上,打制完工后,再用砂轮打磨,这叫“开锋”。在更小的幼年,随着祖父赶集,他曾把我丢在铁匠铺子里,我便看到铁匠打过大铳,用一个十字镐搅铳孔,这是水乡泽国的一门绝活,已经失传了。
我这些记忆被《左镰》勾连出来了,我对田奎这个人物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类似敬佩之情。他与所有成长期男孩一样调皮捣蛋,这并不存在什么过错。一群在河边玩水的孩子,见到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光着身子跑过来,便从河底捞来的黑色淤泥来“打啊,挖泥打傻瓜啊!”孩子们一时兴起,便将淤泥甩到他身上,喜子正好18岁,裸露的生殖器发育正常,孩子们便往他的隐私处扔,妹妹欢子拿着衣服给他遮羞,为他挡在前面,哭叫着讨饶。在“我”和二哥回家吃饭时,喜子的父亲刘老三气冲冲地进门告状,“我”把责任推给了田奎,未必是他带的头,因为他家成份不好,掺杂其中做了坏事,“我”和二哥随口扯上了他,这也是当年地主崽子自然要承受的命运。
贫下中农的刘老三怒气冲冲地找到了田千亩,其子田奎受到了最严酷的惩罚,父亲砍掉了他的右手。他最大的过罪,就是用正常孩子的手,去欺负一位智障者,这样的错误,成长的男孩应该都犯过。作者用刘老三闯进“我”的家门做了铺垫,无需往下写得那么血腥,艺术高超的“留白”,足以令人信服了。幼年时,我同样犯过《晚熟的人》中的旁白者“我”的过错,放学去挖猪草,贪玩忘了正事,听到母亲呼唤声,才知篮儿空空,这时急了,只能急中生智,用几根树枝把篮底衬起,树枝上盖上薄薄的猪草,回到家里把篮子往猪栏里一丢,算是交了差,如果恰巧被母亲发现,一定会挨顿饱揍。显然,《左镰》中的“我”用一个下午只割了一斤草,全家人嘲笑我这个“劳模儿”,说明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的话生动又形象:“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这时“我”拒绝了姐姐带我,便去坟墓上看田奎割草,他给坟头割草像在剃头,割得仔细,“我”在旁边看着,只见他右手绑着铁钩子,比一般人的手还要灵活。“我”与他进行了一场关于“蛇的对话”,那条蛇有一扁担那么长,头上有冠子,紫红色的,还会发出青蛙一般的鸣叫之声。作者描述这种蛇,同样一点不差潜藏在我幼年记忆之中,我们把它称之为“鸡冠蛇”,认为它最喜欢藏身在鸡冠花下。围绕它还有个传说,它遇到人,便会伸长脖子与人比个高低,如果那人矮过它,它就会下口咬死这人。
是不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赤链蛇,方言称之为“火三更”,我在《四十岁的一对指甲》中详细描写过它。有一年我母亲和妹妹在厨房做饭,它钻出洞来,我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拿着火钳,硬生生地从洞中把它拖了出来,捣毁了它的洞,挖出了连成串的雪白的蛇蛋。只是它没有鸡冠,我至今闹不清楚,世界真有这种蛇吗?如果没有,我们与莫言先生的故乡相差几千里之遥,怎么会产生同样的传说,看来民间文学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这样的对话暗喻着什么?我看到的那条蛇又是指代什么?总之,这不是一般的闲笔,这种写法使我想到了海明威先生《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对白。
“我”问:“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
他答:“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少年人,当父亲用刀剁断他的手时,他从身体那种钻心的剧痛,还有心灵中饱受的重创中,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住自己,竟然如此云淡风轻地讲起这段无比残忍的过去。
经过了如此磨难的孩子,在厄运的锻炼下,生命犹如打铁匠那种铁花四溅,残酷却耀眼的景象,我毫不怀疑,他最终将成长为一个生命的强者。
还有一位女性即“我”的三婶顾双红,她这种挥之不去形象让人回肠荡气,久久不能忘怀,这种人物诞生之时,即为文学经典。我多少有点遗憾,作品名《火把与口哨》稍嫌直白了一些。
我不知道莫言先生是不是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蒲公曾描写过一个出神入化的口技女药师。三叔是个矿工,机缘巧合,在车站救了口吐绿汁的顾父传胪,他绝妙的口技,征服了高密城第一美人:“第一美女岳海玲, 第二美女孔海蓉,第三美女邵春萍,三个美女加起来,比不上蜡烛店里的顾双红。”这是高密城的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的,三叔得意地向“我”炫耀。哪知到了顾双红家,碰上几个混混,“吹的是专门调戏妇女的‘狼哨’,”用口技挑逗高密第一美女,这下三叔便用“鹰哨”与他们斗口技,显然“鹰哨”是专门压制“狼哨”的,那三人皆不是对手,一个回伙不到败下阵来,便被矿工三叔收服了。不仅帮他抬嫁妆修车,还成了接亲中的一员。在三叔的新婚礼上,连着镇上的第二大秘书杨结巴,结成“沙窝五耳”异姓弟兄。三叔即兴用口技表演印度电影《拉兹之歌》,作者这样描写:“还在于他能即兴地在基本旋律之上进行变奏,在于他对声音的丰富的想象力,让我们听着是那首歌,但又不完全是那首歌。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花丛中忽隐忽现,使她的美丽添加了神秘;就像月亮在云中时隐时现,使它的光辉增添了含蓄。”杨结巴同样即兴表演了茂腔戏曲。
作者不露声色地在这部作品中交代了时代背景,三叔父母一同死去,只能用麻片和破絮掩埋,顾双红父母则是上吊自尽,把自己的屋子当成焚尸炉,三叔遇矿难而死,尸骨无存。三婶凭吊之时,让同行人先走一步,她希望与三叔独自待一会儿,这里口技再次闪亮登场,作者写到,“三婶吹出的哨声,起初无节无奏,听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的哀鸣,但接下来便无比的婉转与抒情,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然后又变调成急促的旋律,仿佛一只小鸟看到巢卵遇险时在低空的盘旋呼叫。后来又慢下来,旋律很是耳熟,很像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那段‘北风吹’。”口技,作品中至少写了5个相关人的口技,互相映衬,由此道出了他们相亲相爱情到深处的精神本质。
顾三红不仅身世悲惨,自身厄运连连,当三叔故去后,三位青年跪在她面前,求他原谅,并愿意为她抚养两个孩儿,顾双红决然地与之一刀两段,作者不用交代,明眼人便知他们从前欺负过她。儿子被狼叼走,女儿被怀疑骗吃了拐卖人贩子的花婆子的糖块,遭受不了冤枉,小小年纪喝农药自尽,以死还自己的清白。孤身一人的顾双红,突然买来五斤煤油,将旧衣服撕成条,“又找出一床旧棉絮,搓成棉条……将那六对大蜡烛用斧头剁碎,放在东边那口铁锅里, 然后在灶里点燃劈柴,开始熬煮。”让“我”“买一个三节电池的电筒”,准备好这一切后,在一个夜深人静之时,我尾随其后,找到了山崖上的狼窝,用不可逼视的电灯光,照着十几条狼眼闪烁的绿光,这时作为母亲的顾双红,大叫儿子的名字,用斧头砍杀了公狼,结果了母狼,杀死了小狼崽,铁血母性复仇的完成了,形象在那一刻便丰满起来。从狼窝里捡回儿子的鞋子,埋在丈夫的坟旁,诸事已了,她穿上新娘装,平静地躺下,哀莫大于心死,“神仙也治不好不想活的人的病,”七天而去。
我其实是在避重就轻地陈述这个故事,顾双红命运的多舛而让人伤感,更被她的坚强所震撼。她一次一次地遭遇命运的不公,想到她跪在父母焚毁倒塌屋子前,说的“死了也好,活着也是受罪”,当他失去一切之时,绝地反击复仇,这是对命运不公时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最好注脚。
这是个悲剧,渗透着永恒的魅力,她因为最后的一击,成为经典之作。
3.以荒唐岁月对应荒诞的现实,却给人强烈的真实之感

我注意到作者描写在现实社会中真实的荒诞。
在幼年时,我的老家东邻第三家祖父,听我爷爷讲,他早年时,有一次被一只大鳖咬住了中指,如果被老鳖咬住了人手,是不能强行用什么方式来让它松口的,只能等到阴雨天遇上打雷,让它自动松口,吃饭提着它,睡觉提着它,还不敢随意斩杀,只能让它自己爬回水塘里。如果有人敢报复它,或者煮食了它,全家将会得报应。这样的事,我虽不像小奥那样亲历过,却对如此传说是坚信不疑的。一大堆水乡泽国的奇闻秘事,以至触发我花二十几年的时间,构思创作一部近80万字,试图用寓言体小说呈现一个民族近、现代史的《丢失了的城池》,在这个三部曲中的首部《绣船一号与雄起城》,详细讲述过云梦泽第一水猴子铁胡子,带着一只紧咬手指的老鳖到了临泽城的丽春院,坐上四人青衣小轿,提着它放生长江之边,让它由江归海。而莫言先生在《天下太平》中小奥被大鳖咬住的描写,让我大开眼界,我甚感欣慰,同在一块土地上,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被称为“大帅”的老鳖被捉,让作者高超的艺术淋漓尽致发挥出来了。一对父子打鱼人除了精准撒网的动作,描写的细致传神外,还有村支书张二昆,黑汉子、爷爷、知了、麻雀,一列四节绿皮火车、星云姑姑、侯科长、一胖一瘦两个警察、开车的白脸警察、小奥同学袁晓杰、村里的养猪大户袁武、村里的文书孙奎等一干人和物事,最终落到了两根猪鬃上边,这些人一个个粉墨登场,像上演一台活报剧精彩至极。作者这样描写:“瘦警察那几根被香烟熏黄了的手指,灵巧地捻动着猪鬃。老鳖的眼睛似乎眨巴了一下,众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老鳖突然闭紧眼睛,尖尖的鼻子里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与此同时,瘦警察抓住小奥的手腕,猛往后一扯,在鳖口里受苦多时的小奥的食指,终于获得了解放。”还没完,在捉放老鳖之时,众人发现了老鳖背上有字,细瞧原来是“天下太平”,真可谓绝妙之至,在众人欣慰和严肃的表情中,老鳖身子突然立了起来,像个锅盖,然后滚下坡去,落到河水中消失不见。
不由得想到,我在幼年与邻居家的姐姐,一同捉一只搪瓷脸盆大小的老鳖的情形,小姐姐被逃跑时老鳖飞起的泥浆溅得一脸一身,她哭叫着在齐腰身的泥浆里不屈不挠地与老鳖搏斗了半晌,我们不知怎么帮忙,只会大喊:“把它仰脊!把它仰脊(让它四脚朝天,无法动弹)!”这只老鳖终没有小奥的那只幸运,被邻居大妈熬了汤,按照云梦泽人见者有份的传统,我得了一碗老鳖汤。
如果说,作者对“小奥的大鳖”是一次高超艺术精彩纷呈的展示,而那次“冤魂附体”则是绝妙的展现。谷文雨同村的妇女谷玉珍,把高考显灵的李圣洁老师坟上杏子摘下酿酒,因此被“阴魂附体”,她走到覃桂英家,“谷玉珍声音尖厉地哭着骂着,她的骂是唱出来的……覃桂英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小六趾……我爸爸亲自为你做手术……我妈妈为你垫上医疗费……我亲自陪床为你梳头穿衣……还喂你吃了阳梨罐头……你竟然剪我辫子打我脸……逼我跳井你如凶神……我蒙冤屈死十年整……雪恨我让你鬼缠身……小孩子不知往事跟着起哄,大人们知道往事胆战心惊。”
“那谷玉珍在院子里狂舞疯唱,长发披散,脱下衣服挥舞着,仿佛挥舞着辫子,局面混乱,不可收拾,村里人唯恐不乱,起哄叫好,那谷玉珍愈发疯狂。此时就听得院外大喝一声:打倒资产阶级臭小姐李圣洁!……一个威武的大汉,上身穿一件草绿色的褂子,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帽子,腰系一条牛皮腰带,高挽着双袖,臂弯上戴一个红袖标,宛若天兵下凡。此乃何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谷文雨也!谷文雨口号一喊,那谷玉珍如同受了电击,浑身颤抖起来……那谷玉珍往后便倒,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俄顷,谷玉珍醒来,如梦中醒来一般,问周围的人:我这是在哪儿?”
我在幼年,接触过一些神汉巫婆,我的外祖母就是一个著名的巫婆,关于“过阴”(与死去的人对话),“冤魂附体”见过不少,特别是被附体者醒来后,无一例外地忘记自己前一刻的表现。李圣洁老师的冤魂来向覃桂英索命,被谷文雨当年的打扮吓退,这应该是对当年红色运动最独到的一次刻画描写。我的体会是,作者既不明说“冤魂索命”的真实还是荒谬的,而是以荒唐岁月对应荒诞的现实,却能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之感。
也许作者曾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我想只能是北美的风俗人情和历史文化对我们本土写作者一种启示和参照,而莫言先生笔下的“小奥的大鳖”“冤魂附体”则是我们本民族最独有的素材。
4.一代人的传记,时代变迁中的众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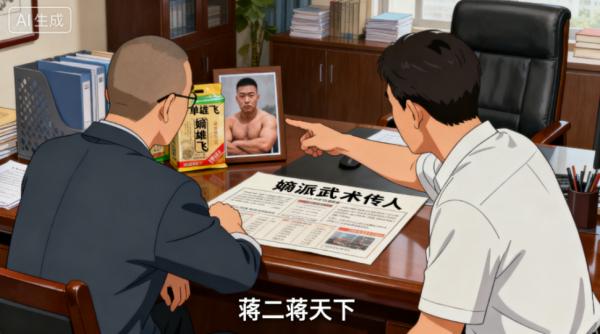
比起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莫言先生描绘的时代与我更贴近,环境熟悉,共情之处颇多,他的作品当然会更好读一些,我一口气读完《晚熟的人》,这部作品讲述的许多人物,有的打中了我的软肋,有的让我思绪万千,有的让我羞愧难当,也有的让我悲悯难忍,一些倔强的灵魂让人感佩,而那种复仇的气概更使人回肠荡气。
由《红唇绿嘴》里的谷文雨,我便想到已经遗忘的经历。几年前,有几个朋友谈及我们这一代成长经历时,我了解到身边的一些优秀者,家族曾背负着成份不好的巨大压力。本人是纯粹的三代以上贫雇农,父亲虽然官不大,也是一个乡镇企业的书记,少年时未必感受到什么优势感。多年后,有朋友给我定性“微型红二代”,我听后很恼火,并予以反驳。事后不免深想,别人一句笑言,为何要动气,说明我似乎想掩饰什么。我曾作为短暂回乡知识青年,颇受大队重视,大队书记已经看中我,要亲自培养我,而我也认为理所当然,处处表现突出,如果时代没有改变,不几年,我将会成为谷文雨那样妥妥的村支书,我很难料想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之途。关于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后来偶尔想来,并无半点“接班人”的自豪感,而是有意选择遗忘。我与谷文雨一样,曾想走当兵这条路,那时的农村青年,要有出路改变自己,别无他途。
要说年少就立志写作,要成为作家,那是理想,当我拜读《表弟宁赛叶》,仿佛看到年少自己的轻狂,穿着喇叭裤,提着一只放着邓丽君歌曲的录音机,在深夜的乡村小镇与一批“怀才不遇”的文友到处游荡,真他文中所说,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肯做,东不成,西不就,满眼的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做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的热情。莫言先生文中一些直白之语,就是父亲斥责我的原话。我至今很难想到,我居然逼他给我买了台录音机,至少两头猪的钱,估计是打着学外语的名义哄骗而来。
我曾主办过许多次笔会,同时也参加过一些笔会,《贼指花》在松花江上演的一幕幕,如同身临其境一样,这些所谓的文化人汇聚在一起,自我感觉良好,油嘴滑舌,互相吹捧、虚伪做作,相处甚欢,皆以为自己是洞悉灵魂的人中之精,实则背后计较利害,权衡得失,精细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旦涉及哪怕蝇头小利,即刻翻脸,加上一群心比天高的男男女女,暗流涌动,争风吃醋,里比多爆棚,上演一幕幕的爱恨情仇。有一阵子,我同样以为自己圆融通透,乐此不疲地玩弄着小文化人的精明,好在清醒得还算及时。
看过莫言先生对蒋二策划的武术活动详细地描写,我一直活跃在这个领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幼年的玩伴,先是瞅准了机会,买了原来属于“我”家的几亩薄地,成了他的地龙文化公司的总部,以作者的名气打造了一系列“地龙”文创产品,精心策划了一场武术活动,其实就是一场比武骗局,蒋天下就是幕后策划者,把过去的对头单雄飞,精心包装成了蒋家爷爷的嫡派武术传人。在这场比武中,看似稳操胜券的他,其实是个为虎作伥的帮凶。中国武术几千年的传承,是侠义、勇气、坚毅和豪迈的代名词,最讲武德,蒋二却把这种传统的武侠精神玩弄于股掌之上,夹杂和包装着民族情绪,成了他赚钱的工具。这些年来,本人同样策划或周旋于这些活动之中,常常处在一种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状态之中,我的生活的另一面,活脱脱的也是一个蒋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罢《晚熟的人》,我无法把它称之为小说文本,它真像是地道的纪实文学,真实记录着这个时代。
我幼年经历的许多场景,莫言先生栩栩如生呈现出来,特别是在乡村看露天电影,除了到四邻八乡反复去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片子,我们湾台前也有一个国营中洲农场,同时也是历史三大赤壁之战传说之地,他们片源大有不同,可以早于我们看到上演的新片,记得《杜鹃山》《渡江侦察记》那个有著名台词“马尾巴的功能”的电影《头裂》也好像是在这个国营农场最先看到的。
至于幼年的饥饿,饿是一样的,老家比之高密那一带,只是情形不同,因为这里是湖地,十年九涝,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个云梦古泽中,荡着破渔船,到处讨生活。
人们常说,损人利己者尚可以理解,而那种损人不利己者最为可怕可憎,覃桂英是两者兼而有之;作为文学中的覃桂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形象,而作为现实中的覃桂英则是让人无比生厌,她因为脚上有赘指,曾受到过伤害,尽管作者没有明写,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她坚持穿鞋下到泥田插秧,心理产生过阴影,她带着幼年的阴影一路走来作恶多端,同样她的一生多厄,惨遭命运的反噬。
《斗士》这个篇名之于武功、“我”的这位堂兄,取得格外贴切,他成份不好,光棍一条,狠斗支书,不遗余力,把村里最能打架斗狠的王魁诅咒到带着全家老少逃往外乡,不敢回家。我们老家就有这样一种人,如果谁惹上了她,就是倒了祖宗十八代的大霉。我们湾台是建在半截废弃的河堤上,另一边的河堤是家家户户的菜园子。这位“骂死人不调面(不重复)”的妇人,拿着一块砧板和一把菜刀,骂一句便剁一下,她可以大骂几个小时,口不干舌不燥,我曾在早年的一篇文章里详细记录过这些骂人之语,真可谓聚古今骂人之大成。
5.站在世界文学之林,出手就是不凡的

莫言先生善于写人,他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几笔下来便有血有肉。《澡堂与红床》中那位像张国荣又像《第八个是铜像》洗脚女的丈夫,寥寥几笔,“我说,小汪,你妻子真能干,你们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他将烟蒂扔到树丛中,有气无力地说:将来,将来在哪里?”直入灵魂。
如同许多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一样,比如2018年波兰诺贝尔获奖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太古与其他时间》,就是一个虚化的村庄,2024年韩国女作家韩江的作品,一直描写大屠杀记忆和伤痛,2025年获奖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同样写个破败的集体农庄,作家皆立足于一点,以点代面,推及全人类。莫言先生一直写故乡高密的这个小小乡镇世界,所涉及的人和事,却牵动几代人和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由此生发出去,直抵人性深处,触及灵魂。我先不说《晚熟的人》有多么高的艺术魅力,只是想说,一个人能站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他出手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莫言先生的语言极有特色,我形容这是一种冷幽默,那种描写,既让人刻骨铭心,又不露声色,还让人过后会心一笑。我早年拜读过他的大作,便留下记忆,现再次拜读,那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这就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内在品质,何况是一位大师。我想到拉斯洛善用长句式的风格,他同样也是在处女作《撒旦探戈》便形成的,一直到现在只是更加娴熟了。
作家是一个上帝视角的职业,他全能全知,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我对一些大家名家,用一种尖酸刻薄之笔,去描写笔下的人物很不适应,我认为真正的大家,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一种满含悲悯和慈悲以及“无我”。记得早年留下过印象,托尔斯泰就莫泊桑描写一对母女被强暴时,作者被自己渲染的情绪所左右,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莫言先生在《晚熟的人》之《红唇绿嘴》里,对覃桂英就是用冷静客观的描述展示给读者看,即使是“我”面对她“卖谣言”,一条2万,两条4万,气极反笑的“我”,本打算拟两条“谣言”回敬给她,“犹豫了好久,”还是回复了“谢谢,我不买。”当然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我”迁移到作者的心境上,然而我认为从一个侧面说明,对笔下的人物,好也罢坏也罢,喜欢也罢厌恶也罢,不带个人情绪客观呈现出来,作者一直把握着一个度,是不容易的,只有高手,使笔下的人物更具有艺术魅力。
我从未想过,在几千里之外的山东高密与我的故乡云梦泽的腹地,有如此多的相通之处,突然想到2022年诺贝尔获奖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写一代人的传记《悠悠岁月》,我并无去搞成一种庸俗的类比,但用万余字的篇幅写《晚熟的人》读后感,并不把它当成小说来读,我认为它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吧——许多事我尽管没有做过,但想过;许多事,也许不曾想过,时代、环境、氛围却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顺便一说,我与经济学家胡必亮先生是发小,他满天飞时,在候机室或乘机的高空上,读完了我的《云梦泽》手稿,也许是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场景,以及我们三代人的成长环境,深深地触动了他,他与莫言先生是在上下楼的办公室,曾一同去过德国,想着力为我引荐这位大家,可惜他突然离去,留下了遗憾。当然,以文会友,也未必要面对面地交流,通过《晚熟的人》不同样是一种神交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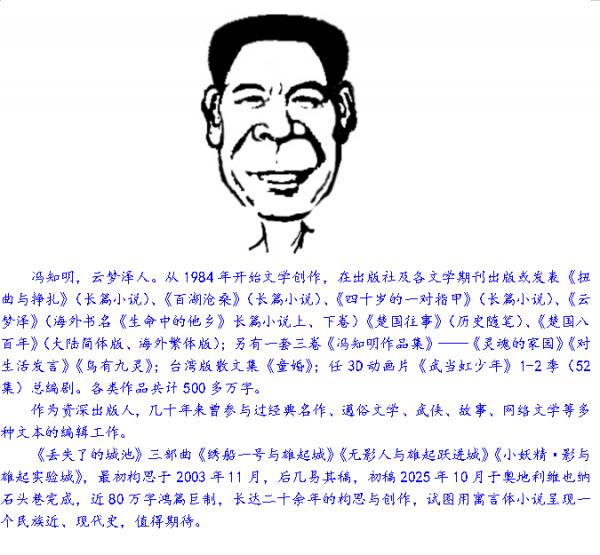
2025年11月10日星期日 法兰克福美茵河畔40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