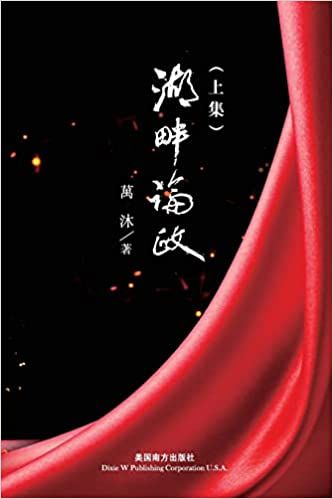那飘不去的炊烟
那飘不去的炊烟
萬沐
每当我深秋看到多伦多升起的烧秸秆的烟柱,便会想起我故乡的炊烟。
我的家乡是在渭北高原上豳地的一个村庄,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村民聚族而居,春种秋收,人歌人哭。“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女儿四岁那年从村里来到了重庆,记得她感到很不适应,总是喊着要回去,但又回不去。幼儿园教孩子画画,她学得很快,但画的画总是一个内容。就是一座小房子上,飘着袅袅的炊烟,一个小娃娃拿着一个红苹果,站在房子前。我知道,这是一幅写实的画,这个房子的炊烟,就是我家果园里的炊烟,而这个娃娃就是她。
大概在小学女儿二、三年级的时候,家里来信,说厨房已经换上了天然气炉,再用不着烧柴火了。显然,这是在报一个喜讯。但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却突然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回家再看不到炊烟了。她妈妈说她矫情,因为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其实,大概是不知道她的一颗思乡心,和一颗独特的诗心。
女儿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巴渝,一切都变了,显然是很不习惯的。我当年到重庆的时候都二十多岁了,都很不习惯,何况她一个小孩子,连重庆话都听不懂。女儿经常和我说家里的人,她的大黄狗,雨后的彩虹、院子里月光,还有炊烟,以及她跟着曾祖母做饭的各种欢乐的事情,我知道,这才是她要的生活。离开村子前,她说要家里所有人都去,把门前的树带上,把周围的孩子都要带上,重庆还要有烟囱。她到重庆后,和小孩子做游戏,总是模仿着在老家厨房做饭的样子。不仅比划着揉面,还要比划着烧火,一个游戏做下来,似乎非常忙碌。
一次,我记得女儿突然站在床上,即兴朗诵了起来,语言十分流畅,仿佛是在背一篇文章,其实是她在口述一篇文章,她说叫做《遥远的故乡》,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其中就有一段在夕阳里,村中炊烟袅袅、绿树环绕的景象。我至今还记得她穿个背心、短裤,身上披条毛巾,站在床上,口中滔滔不绝的样子。
女儿三年级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就叫《炊烟》;
“那是什么?那就是炊烟吧!
------
它飘呀飘,
飘到了天上的云海里,
飘到了彩虹的桥梁上,
她一直飘到
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它像淘气的孩子,
在跟你捉迷藏。
又像一个个美丽的小天使,
正欢乐地飘向上帝的身边,
它代表着人类的安详
和上帝赐予的和平。
显然,这写的就是我们村里的炊烟。
等女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成了鲁迅文学院少年班的学员,她已经读了很多古诗词,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草阁居士”。我想这除了她“附庸风雅”之外,肯定是带着对家乡村居生活的想念和一种回到家乡的期待。
我对家乡炊烟的感觉虽然没有女儿那么诗意,然而也有无可代替的亲切,和关于过往饮食的记忆。
在我童年的时候,似乎都是炊烟美好的记忆,因为我说要吃的时候,我奶奶马上就要给我下面,随着灶间燃烧的柴火,炊烟飘出屋外,我要么吃白面,有些时候还要炒鸡蛋吃。而且,我坐在炕上吃的时候,不许其他人逗我,如果逗我,我就要骂。但我发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能这样吃。等到大了以后才知道,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家里人千方百计给我开的小灶。其实,当时我们那一带,已经有人饿死了。
我那时候除过受家里呵护,叔祖父一家也很宠爱我。他们家人口少,生活要比我家好一些。每当叔父星期六从中学返家的时候,我就要去他们家吃,看着烟囱里袅袅的炊烟和叔祖母在锅边忙碌的样子,我知道就有一顿好的要吃了。想想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但往事在我心里并不如烟。叔祖父过世的时候我在大学上学,回家后才知道,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大哭了一场,并且在此后半年一直感到很难受。据家里人说,他去世前,还在念叨等着我回家过年。叔祖母是我在重庆时过世的,我之后回家的时候,她的坟头上还留着新的纸花,而我与她已经永远天人相隔。现在想起,仿佛仍然看到他们和我一起吃饭时,那亲切温暖的样貌。
但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再看到炊烟,心中就充满了哀愁。除过觉得高粱面很难吃,还知道,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家已经连难吃的高粱面都吃不起了,野菜也被吃光了,甚至传来北塬上一家人活不下去,跳井自杀的可怕消息,更可怕的是,我姑姑的村子里,一个人因为吃得多,长期被家里人嫌弃,最后在生产队饲养室铡刀下自杀的消息。据说,在人头被铡下后,身子疼得还爬了十几步,满地都是鲜血-------
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些思考能力,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搞人民公社?为什么劳动人民过得这么苦?远远不及老人们口中的“旧社会”,还有我们一家人都天天像牛马一样辛苦劳动,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饭吃?而公社书记经常骑自行车带着他的医生情妇,经常来村子里又吃又喝,走的时候还要白白带走很多东西。我想这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吗?为什么老师在课堂上批评资产阶级法权,而现实中这些干部却依旧这么干呢?那时候很喜欢的两本书是《革命烈士诗抄》和《宋诗一百首》,《革命烈士诗抄》让我向往革命改变社会的不公,希望自己能遇到恽代英、瞿秋白这样的人,请他们解答我的疑问,即使遇到殷夫、陈辉这种正直的人,我也会觉得很棒。同时,宋诗里张俞的《蚕妇》、梅尧臣的《陶者》和范仲淹《江上渔者》对社会的疑问,更是给我这种愤怒情绪添了很大一把火。
然而,周围是沉默的。与我有同样命运,或者命运更悲惨的人,即使烟囱里无法再冒烟了,却是不会有我这种愤怒的,除非几个老人偶尔骂几句。我那时还很爱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从中得到答案,但读后觉得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和毛主席说的完全相反啊!我感到既困惑又愤怒,就把我对社会不公的的愤怒发泄到了我自己装订的一个粗纸的本子上,写了很多的时评文章。现在想起来,虽然没啥理论深度,但道理说得还真痛快。可怕的是,我父亲发现了这个本子,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揪了起来,他一脸暴怒,说我是把全家人要逼到死路上去,他和我爷爷、我奶奶讲了我指责社会不公道的“反动”内容,祖父母也被吓得不轻,三个人骂了我半夜,最后父亲把我那本“政论集”也放进炕洞里烧掉了。我当时尽管觉得很可惜,但却没有理由制止他。
初高中阶段村子里的炊烟是苦涩的,人情也是很苦涩的。尽管那时已经到了文革结束的前后,但我家的成分不好,依然是政治贱民,甚至连累到我养的一只小黑狗也成了“政治贱狗”。我那只狗很乖,有些时候人断炊,牠也跟着挨饿,记得有一个春天,已经一天没粮食吃了,第二天早上,我从外面买了面粉回来,炊烟才从烟囱里升起。从锅里捞出来的第一碗面,我就是先给小黑狗吃的。小黑狗很通人性,看到有东西吃了,和全家人人一样快和。
小黑狗平时爱躺在大门口的门洞里,有人路过,总要“汪”“汪”两声,但从来没有冲出门咬过人,然而,就这“汪”“汪”两声却惹来了大麻烦。因为有很多人每天路过我家门口,有人仗着他们是贫农,就故意挑逗我的黑狗,并拿铁锨或者镢头在狗面前的台子上砸。这也不只是无聊,其实就是挑衅找事。尽管从血缘上来说,大家关系并不远。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似乎阶级成分就决定了一切。也许他们是在发泄旧社会过得不如我家的那股怨恨,所以就将我的小黑狗也当成了“阶级敌狗”,并对小狗“汪”“汪”声大做文章,向村子里的李姓革委会主任告状,说我的小黑狗咬贫下中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很不得了的罪名,我也被吓得不轻。因为另一个公社就有一个地主家的狗因为咬了工作队的干部,最后狗被押上拖拉机公开处决的可怕传说。据说在处决了狗返回时,架在拖拉机上的大喇叭却放了一曲《国际歌》,当时谁都不敢吭声,但这个荒唐的事情后来却成了冷笑话。
鉴于小黑狗只要门前有人走过,就要叫,即使栓上大门,也照叫不误,而门外依然有贫农故意挑逗小黑狗。当时我实在没办法,怕我的小黑狗有一天被人打死,便忍痛将牠卖给了村子里李家一个叫民民的人。
一个晚上,我带着我的小狗去了沟底下民民的家,民民见我把狗送来了,给了我一支他卷的烟,我坐在炕沿上抽了两口,眼泪就流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这支烟太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很难过,舍不得我的小黑狗。民民买狗是因为他和他哥在几十里外的山上为一个村子里守树林,需要有狗为他看家。可能过了一年,有村子里人去民民家,说我那只小黑狗已经长成一只很大的狗了,还说民民给牠吃得很好,我听了心里才安稳了一些。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记着我把小黑狗交给民民后,我离开时牠急躁的眼神和愤怒的叫声,我扭过头,不敢看牠,哭着离开了民民家的院子。
以后,听说民民生活艰难,过得很不开心,在一个除夕的夜晚,上吊自杀了,我那只黑狗的情况也就再没有人提起了。现在,女儿在欧洲,我平日替她喂她那只猫,猫很挑食,很难侍候。但想到当年,我喂我的小黑狗,牠因为我给牠的一碗面那种满足的表情,把那只盛面的小瓦盆舔了又舔,还摇着尾巴的样子,就感到非常心酸。
民以食为天,在我的村庄,很长时间,人们的最高目标不过就是生存。男人日出而作,但日落也不能息,仍有很多的家务活要干。女人们除过在地里干活,还要在烟熏火燎中准备一家老小的饭食。无论早上,中午,还是傍晚,村子总是炊烟袅袅,炊烟里飘着不同年月饭菜的气息,有香甜,也有苦涩。在女儿的心中,是一种田园的诗意,在我的心里则是亲切中混合着各种酸甜苦辣。
炊烟是我们农家的日常,也是我这位离家多年后,对家乡独特的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也传递到了我的女儿。这种审美的背后是生命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象征。我一生漂泊,但离得再远,只要提起渭北的老家,那一缕缕炊烟就马上浮现到了眼前。
购买《侨领》等书请点击:有折扣:萬沐新书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