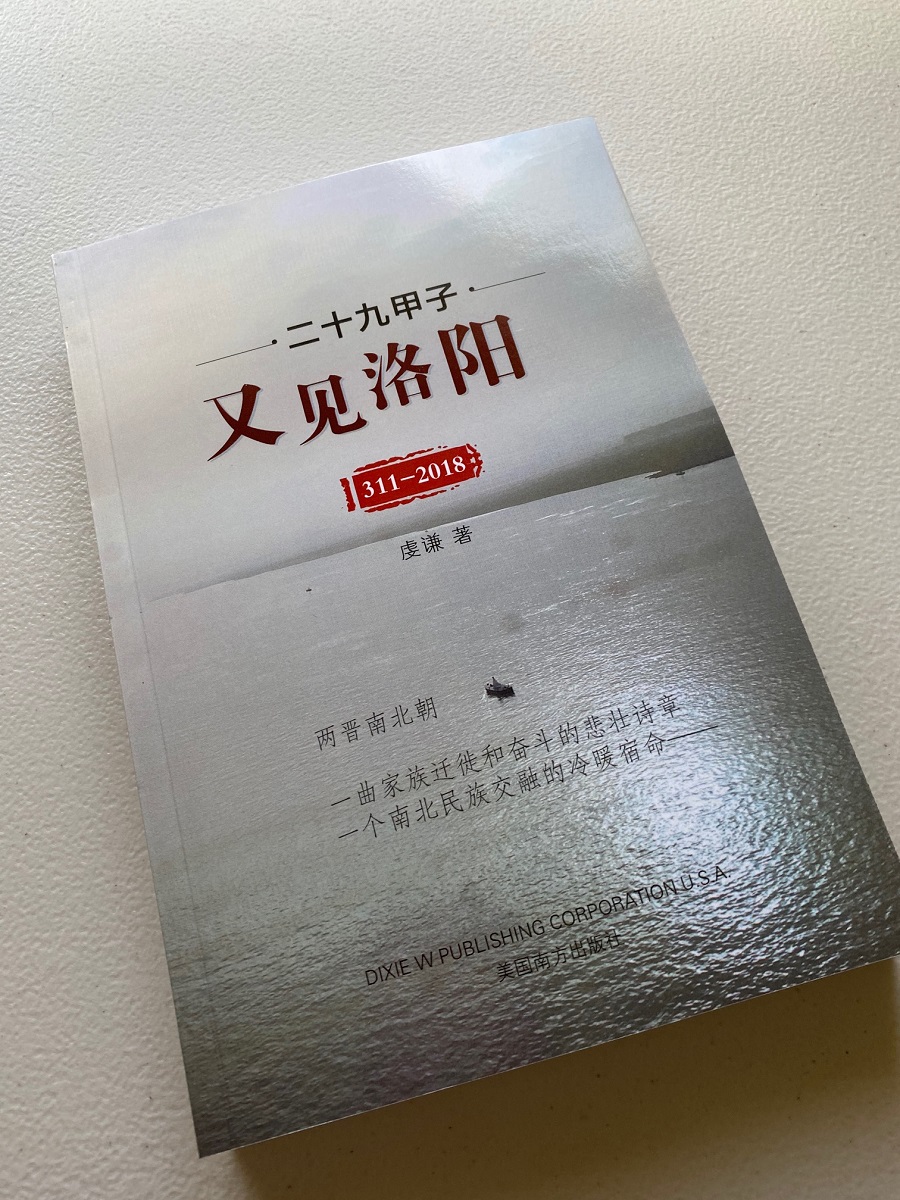散文:不到阳关非好汉(附《巍巍玉门关》链接
在西安和洛阳行之后,一块沉沉的石头从我心头落地,因为我完成了多年夙愿:探访我们古代文明的东西两大中心。然而,嘉峪关、河西走廊、阳关、玉门关,犹如一条迷离而又若隐若现的彩带,总在我脑海深处飘拂,不肯离去。
2025年九月,经过三个多月的细心准备,我终于敲开了中国西北门户兰州,通过她进入西北长城最后的关隘:雄立于祁连山北麓的嘉峪关,进而到达敦煌。
从敦煌继续西行七十公里可至阳关。敦煌离玉门关则有九十公里。由于未能确定可靠的交通工具,阳关行程未卜。至于玉门关,AI告诉我:路远且有潜在危险!的确,从敦煌到阳关、玉门关,要经过类似无人区的荒漠。一位出租车司机甚至告诉我: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可能困在那里回不来!正值可怕的炎热季节,我很挣扎,几乎要放弃。所幸,内地亲戚及时查询到了一班专跑敦煌和阳关玉门关的可靠汽车。就这样,暌违几十年,我宿命般地又一次来到显得十分老式的公共汽车站。开车领队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五十多岁,知识渊博,十分儒雅。
这一路,我们的车穿越了绵延到天际的黑色荒野和彩色戈壁沙漠。虽然荒凉,但仍不时可见高高的白色风力涡轮机在蓝天下转动,气势雄伟。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阳关。
我抑制不住心跳!如我想象中那般,阳关果然是个古风十足的景区。走进景区大门,就有悠悠的古琴声传来,我听出那就是《阳关三叠》。这首古曲诞生于唐代,取材于并演绎了大诗人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我儿时就知道这首曲。走出都尉府,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场地,有仿古建筑和城墙。汉代关城早已不在,这里就是仿古而建的阳关关城。《阳关三叠》在整个关城的每个角落回荡,仿佛是历史的回音绵延不息。
出了城门,在汉代就是出国,通往西域了。我步出关楼,诗人王维的雕像便出现在眼前。王维衣袖飘飘,目光远眺,左手持酒杯,右手指向远方。王维雕像旁有一棵迎风飘拂的垂柳。显然,这是着意重现其诗中意境:“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七绝里的“渭城”是今陕西咸阳,与阳关相距一千六百多里,是王维双眼无法穷极的天外;而友人元二的目的地更在阳关之外!我就想,在人类高科技将自然的原貌赤裸呈现出来之前,在生活各方面非常不便利,甚至不安全的古代,人们需要丰盛的想象力,需要坚强的浪漫精神来平衡天高地远的阻隔,平衡严峻的现实。他们的文字往往能穿透巨大的时空和生活的艰辛,到达祥和平安的彼岸。《送元二使安西》,或称《渭城曲》,就是这样被创作出来的。而阳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广袤的悲凉,也不乏刚硬和浪漫温馨的地方。
公元前121年,汉匈激战之际,汉武帝启动了长城的修建。在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后,为巩固帝国西陲的安定与繁荣,高瞻远瞩的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并在最西端的敦煌设立了玉门与阳关南北两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所有地名,经久未变。
离开王维塑像,阳关烽燧遗址便出现在远处的高地。此日之前,我曾无数次于不同的季节,在彩图中,在诗歌、文献上,在梦里,见到这座奇丽的烽燧。而今,我怀着近乎朝圣的敬畏之心,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走了二十分钟,这座梦幻般的烽燧,不知何时自然地滑落了她曾经的面纱,清晰地向我裸露她古朴而神奇的面容。这是一副高于人类语言能力的优雅容貌,一个超越时空维度的倔强存在。她沉默而坚定,在强劲的风沙中高高矗立,扼守长城南路终端。两千多年了,她依然生动地揭示着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存在与发展,以及这存在发展深处的逻辑。
在阳关烽燧的四周,绵延起伏着类雅丹地貌和色调,壮阔而秀美。一条木制的笔直大道——阳关大道——在一片金色的沙漠上伸展,标识着古代阳关大道的遗址。这是一条张骞、李广利将军和玄奘都曾走过的大道。离大道不远,便是隶属于阳关都尉府的军营遗址……我站在阳关景区的高处放眼而望,见这一切犹如众星拱月,簇拥着这一带的最高点——阳关烽燧。这座烽燧,隔着库姆塔格沙漠与阿尔金山遥相呼应,历经岁月里无比的物质锤炼,已然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一个文明的超然殿堂。
我激动,并为自己深感庆幸。心志的坚持,让我终于目接烽燧,神交阳关!
(该文原载《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转发于《阳关文学》杂志)
注:散文《巍巍玉门关》发表于今天(11/07)的《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51/9109029?from=wj_catelist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