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书名之外还要个副标题,建议加上:在风雨中安放学术
余英时这部回忆录教会我们如何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做出与学术相容、与人格相符的选择,在面对政治巨浪时,把“判断”与“研究”摆在各自位置,把“尊严”从抽象词汇变成日常功课。一位政治历史学者的价值,在于他用一生把一套可操作的秩序留在了我们手中
在大时代的列车与岔道上——评《余英时回忆录》
马四维,中华书法评论,2025年10月5日
读《余英时回忆录》会强烈感到这不是一本单纯的忆旧之书,而是一部“以记忆复位学术”的时代见证。书中自述与旁证交错,既有作者口述的亲历,也有编辑者廖志峰在《开往普林斯顿的慢车》中记录的沿途细节:2018年在普林斯顿的长谈、书房的留影、扉页上的“河西走廊口占”、以及多次“正在寻找老照片”的电话回响。这些碎片把一个“知识人”(余英时自称常用的词)最在意的事——学术与人格——安放在三段关键的时间坐标上:1949前后、1969前后、1989前后。若不在这三处节点上把叙述拧紧,我们就读不懂这本回忆录的历史密度,也读不懂余英时作为一位“政治历史学者”的独特形态:他既在政治的暴风圈外保存了学术自由的火种,又在历史的长期线上检验政治抉择的后果。
《回忆录》里最令人难忘的篇章之一,是他从内地辗转至香港,在新亚书院遇到钱穆、唐君毅诸师的那一段。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青年而言,这既是“离散”的起点,也是“入学”的起点;离散让他与故土的制度现实拉开距离,入学让他在传统学术的“近身教养”里扎根。钱穆教他的,并非单一道统,而是一整套“为学即为人”的实践品格:治学要有根柢,做人要有定力,立场可以鲜明,情绪必须节制。余英时后来屡屡回忆,这一段“在风雨之夜仍有灯可依”的生活经验,使他相信中国学术的现代继承并不靠口号,而靠具体的制度与人格:一间书院、一位老师、一张书桌、一套读书方法。这些在1949年的去留之间被重建起来的“最小单元”,在余英时此后的学术与公共发言中反复显影。

也正是在这条去路上,许多人提出一个尖锐的反问:倘若没有1949的出走,余英时会不会像陈寅恪那样“倒在1969”?这不是一句修辞,而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历史设问。《回忆录》虽然不做“平行世界”的推演,但材料提供了判断的底板。1960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界处境之艰,史不必再赘;陈寅恪以近乎全盲之躯完成《柳如是别传》,1969年病逝广州,成为那个时代知识人精神史的一个终点。若余英时留在大陆,他是否也会在高压体制中失声、受挫、甚至中断学术?从他在书中处处强调的“学术即人格”的立场看,他决不会以口号换平安、以沉默换通行;这恰恰意味着,他很可能付出与陈寅恪相当、甚至更为惨烈的代价。换言之,1949的出走,既是历史给他的现实安排,也是他主动的价值选择:把自己安放在一个能继续“学术生活”的制度空间中。只有在那样的空间里,才有可能酝酿他后来整个学术体系的生成——从晚明思想史到现代新儒家,从“士与中国文化”到“历史与思想”,从经世之学到心性之学的再对话。
时间跳到1969前后,《回忆录》在写到赴美求学、在哈佛受教及早年的任教经历时,语气并不喧哗,却处处可见一条内在的弦:学术的进路不是“题目叠加”,而是“问题深化”。他受教于杨联陞等师,留意的并非某一派的“正统”,而是史料的缜密与问题的历史生成。他反复提出“由思想入史、由制度观人”的互证方法,将思想史从“抽象观念史”拉回到“士人群体的社会史”。也正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逐步把近代中国知识与政治的“纠缠叙事”建立为一个可研究的对象:晚明党社运动如何重塑士大夫的公共伦理,清季新政如何催生现代学术共同体,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三角张力如何塑造20世纪的知识人自我。站在1969年,美国也在巨变:冷战、越战、校园运动与新左派席卷学界。余英时并未被“风潮”吸走;《回忆录》中可见他清楚地划定边界:政治可以构成研究对象、可以构成道德判断的场域,但不可以吞并学术本身。正因如此,他在美国学界建立的是一种“兼容而不混淆”的范式——既能用现代学术的工具进入中国史的深处,又不把现代理论当作唯一的裁判官;既能与英语世界对话,又不在中国史实与汉语文本面前丢失细节。这种范式在1969年前后定型,它不是“避世”,而是为学术争取到“在政治之外说真话”的工作间。
把时间推至1989前后,这一段在《回忆录》与后来诸多谈话录、演讲集中都有清楚记述。1989年的政治巨震,让“知识人”与“公民”的角色骤然重叠,也让“学术共同体”的伦理经受拷问。余英时没有回避,他明确站在“人的尊严—学术的自由—政治权力的边界”这一条线上发表判断:国家可以谈秩序,但不能以暴力摧毁言说;大学可以谈中立,但不能以沉默耗尽良知;历史学家可以谈复杂,但在生命面前必须先做出基本的是非判断。若把这与他1949年的去留、1969年对学术边界的维护接连起来看,1989年不是“临时表态”,而是他长期学术—人格坐标的自然延伸。也因此,《回忆录》并未将1989年收束为“个人情感史”的一章,而是当作“知识人共同记忆”的节点来处理:那一年以后,他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自由主义价值、公共伦理与大学制度的思考全面展开;这不是“转向”,而是“显形”。
这三处节点共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时间链:1949年,选择可言说的制度空间;1969年,建设学术与政治的防火墙;1989年,在大的是非面前确认知识人的公共角色。沿着这条链去读《回忆录》,我们也可以回答前述的假设题:若没有1949的离开,他会不会“倒在1969”?答案或许并非“必然”,却非常“可能”。从他人格的硬度、学术的自持与在关键时刻的表态来看,他不可能在一个系统性压抑学术与言说的环境中“安静地伟大”;他会抗拒,会发声,会承受代价。陈寅恪以“忍而不隐”的方式挺过了他的最后十年,终以“文史合一”的巨构完成自我;余英时则借助地缘与制度的选择,完成了另一种“忍而不隐”——以持续四十年的学术生产、以跨语言的大学讲席、以“知识人”的公共写作,累积成一种更广阔的影响。两条路径殊途同归,都是在“不得不忍”的时代里为学术保存了尊严,只是代价不同、形式不同、影响范围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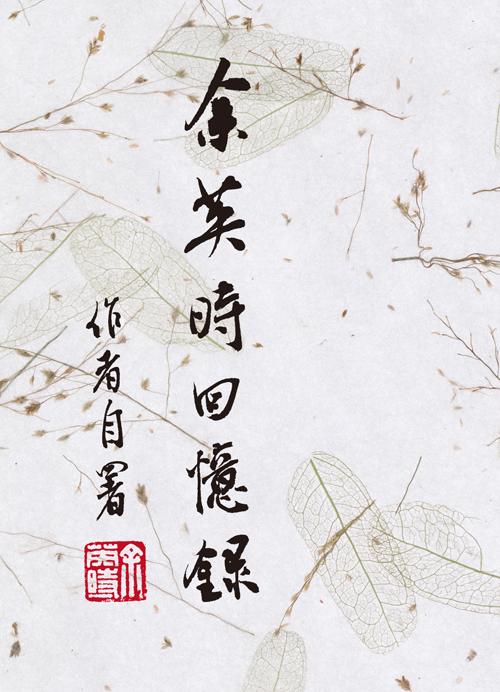
《回忆录》的可贵,还在于它并不把自己写成“命运剧”,而是细致地展示生活如何与学术互相嵌扣。书中多次提及钱穆,提及新亚书院,提及书院之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张力与互补。读这些段落,很容易看出他与老师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选择正确”的一脉相承:钱穆以建制中的“独立空间”抵御意识形态化的大学,余英时以美式大学的制度弹性守住学术的底线;两代人都不把“传统”当作口号,而把它当作一种“可传递的生活方式”:以学术为职业、以道德为边界、以公共言说为担当。余英时曾自称“尊严的知识人”,这不是荣耀的勋衔,而是一份自我约束:不把学术降格为政治修辞,也不把政治抬举为学术真理;在必要时为基本价值发声,在平常处回到文献、回到课堂、回到史学的基本功。
从文本形式看,《回忆录》与廖志峰的编辑手记互为补章。后者的“慢车”叙述,给读者提供了进入作者私人生活的路径:书房的门“极少让人进入”、扉页那首1978年深秋的《河西走廊口占》、在普林斯顿后院成林的竹子、一次次“怕你找不到我”的电话;这些细节都不是猎奇,而是在提醒读者:一个学者的历史感不是抽象出来的,它在他的生活习惯、时间管理、语言风格中长期淬炼。《回忆录》因此具备两层时间:叙述的时间与编辑的时间。前者是作者从记忆取材的线性流动,后者是编辑在现实中奔走、在“马拉松”的耐心里把散落的碎片缝合起来的过程。二者交叠,使这本书不止是“我的一生”,更像是一种“如何将一生化为学术”的实践记录。
评一本回忆录,不能只谈“其人其事”,还要问它为我们的理解增加了什么。对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回忆录》至少提供了三条有用的线索。第一条,是“士与制度”的双向观察。余英时在书中反复谈到“士”的精神传统,但他从不神化“士”;他强调,士人伦理之所以能在帝制时代维持张力,是因为有一定的社会与制度空间(科举—书院—文会—家族)作为支撑;当这些支撑被破坏,士的伦理也会变形。这套思路在他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考察中延伸为“大学—出版—媒体—公共舆论”的现代支撑网络。《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作者不是在“学术外”才想到这些,而是在自己的生活史中实践出来:他之所以能持续写作、能在1989年后发声,恰恰因为他拥有一套可运转的制度支持系统。第二条,是“史与心”的互证方法。余英时强调“思想史必须落在史料学上”,但他也从未放弃对“心性—价值”的追问;《回忆录》中的自我追述并不回避立场,反而在立场之内不断用史料作校准,这种写法本身就是思想史写作的范式示范。第三条,是“知识人与公众”的边界重划。书里对1989年的处理表明:知识人介入公共议题,不必把自己变成“政论家”,但必须在关键处给出基于学术与良知的判断;这种判断的公开化,不是为了制造“敌我”,而是为了守住话语共同体的最低线。
笔者认为,余英时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知识人,都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跨越了他的时代,人格、学术,俱成不朽。“超越”不是夸赞的形容词,在他这里有具体的指向。所谓“超越时间”,并非无视时间的变化,而是在不同时间点上保持一种可被识别的价值坐标;“超越空间”,并非脱离具体国族,而是在不同制度空间里保持学术的可迁移性与可沟通性;“跨越时代”,并非拒绝时代,而是在时代转折处提供历史的深度与道德的方向。《回忆录》证明,他确实做到了:1949年的去留不是逃离,而是为学术另辟空间;1969年的坚守不是退隐,而是为学术建立边界;1989年的表态不是冲动,而是对长期坐标的兑现。将这些放回他与钱穆的师承关系里看,“立场鲜明、选择正确”不等于简单的“站队”,而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理性——知道何时应当说“不”,也知道怎样把“不”说得有分寸、有根据,能经得起时间的审核。
当然,《回忆录》也有其“留白”。它并不试图在一己经历中囊括所有争议问题,有些敏感处点到为止,有些学术恩怨不作展开。这既是回忆录体裁的自我边界,也是作者一贯的行文审美:把重点留给“问题”而非“八卦”。读者若想在人物关系与学术纠纷上“看热闹”,可能会感到意犹未尽;但如果把这本书当作进入余英时学术世界的“索引”,再去读《历史与思想》《士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家思想的兴起》等论文集,去读他对钱穆、胡适、殷海光、唐君毅、牟宗三的系统讨论,乃至重读他早年关于晚明党社与清初思想的研究,就会发现这本回忆录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脉络与钥匙。
我尤其喜欢书里关于“尊严的知识人”的几段自述。余英时并不把“尊严”理解为离群索居的高蹈,而是理解为“说清楚自己所知、所信与所不为”的能力。尊严不是姿态,而是方法:在史料上精确,在概念上克制,在判断上负责任。把这三点揉进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他同时被视作“政治历史学者”与“思想史大师”。“政治历史学者”几个字,若放在一般语境里,容易被理解为“立场先行”;而余英时的做法恰好相反:先把历史问题的层次理清,再给出政治伦理上的判断;判断不是为了结案,而是为了让讨论在更高的明晰度上继续。这种秩序感,是他给这个时代的罕见馈赠。
最后,把视线回到廖志峰在后记中记录的那些微小瞬间:普林斯顿后院从一株到成林的竹子,书房那张少有人能得的照片,扉页那首“昨发长安驿”的口占诗,以及那句“许多事一言而决”。这些片段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在场”想象,更因为它们与《回忆录》的核心主题相合: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也因此而被赋形。我们在书里见到的并非一位“超凡脱俗”的贤者,而是一位“在历史里过日子”的学者:他也会为一则书名斟酌,他也会为一次访谈改题,他也会因电话线被飓风刮断而失联,但他总能够在下一次书写中,把生活的杂音转化为学术的清音。
《余英时回忆录》不仅可读,而且可学。它教会我们如何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做出与学术相容、与人格相符的选择;教会我们在面对政治巨浪时,怎样把“判断”与“研究”摆在各自的位置上;也教会我们把“尊严”从抽象词汇变成日常功课。如果说书名之外还需要一个副标题,我愿意加上八个字:在风雨中安放学术。对今天的中文世界而言,这八个字并不轻松,却格外必要。读完此书,我们不只是在回望一位大师的来路,更像是在确认一条仍可行走的路径:在1949、1969、1989的节点之外,仍有2029、2039……历史在延长,问题在更替,而一位“政治历史学者”的价值,恰在于他已经用一生把一套可操作的秩序留在了我们手中。
近期文章:
既是一份告别信,也是一份忏悔录,还是一份控诉书
请用文明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也谈最近一份泄露文件
跟着依娃走陕西——读依娃小说集断想八则
译者眼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作家,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想起电视剧里说的:“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
川普起诉媒体、天价索赔,算不算打压新闻自由?
狂热分子,极左和极右本是同一种人
这一场白宫晚宴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值得详加解读
介绍孙立平两篇短文:瘆人危机前景下的“哄你玩”
订正一个民间失实之辞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