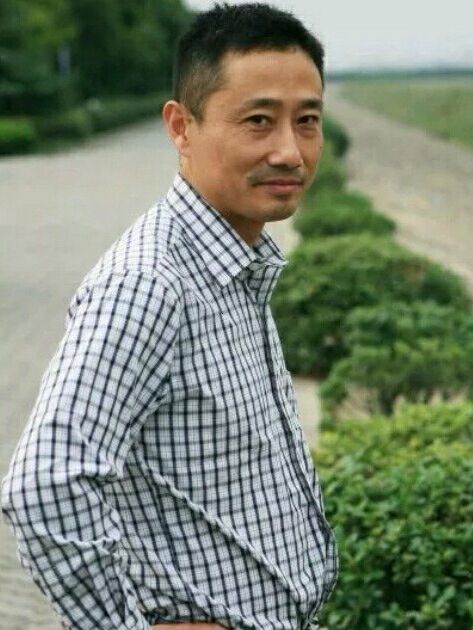东方安澜:食货志(全)
食货志
一 长物志与食货志
早上3:35,睡不着,没有睡意躺床上骨头痛,只得起来,无聊,侍弄那几个茶壶。泡了壶绿茶,把几个茶壶浇淋了一遍。最早识茶壶是从玉霖翁那里开始的,一晃可能三十年了。后来陆陆续续,几个茶壶已记不得年数,但许多年了依然壶色新气糙旺,平抑不了。本来,日积月累的茶油吃进壶面的汗毛孔里,积起来的茶垢覆盖壶面,使壶器看上去光泽柔和,仍而,万物有灵,壶可能跟随我久了,跟我像我,骨子里的糙气总是浮在表面,任尔风吹雨打,不自抑,意难平。脾气脾气,脾无气不伥,气无脾不立,天生一个犟种,奈何!
看来得换一副玲珑一点的皮囊,以期能做个八面玲珑人。反正今生是无望哉,“玲珑”两字与我无缘。今天早起,本来打算敲《长物志》,笔下想写的是“河泥畚箕”、“铰刀”,“缸瓴箸甏”等老家什。后来左思右想不对,这些旧物和当日生活紧密相关,不是可有可无属于精神层面的长物,严格来讲是于器谋食,应该归纳为与民生生计相关的食货类,看来笨皮囊再怎么浇淋,总因娘胎带来的质地不好,怎么侍弄也生发不出通透幽微的灵光。
由此,《长物志》改成《食货志》。本来父亲死了5年,这些老东西早就应该处理掉,但是,在父亲身前,我把铰刀丢了5次,父亲去外面不声不响捡回来了5次,爷俩脾气扛上了,差点甩拳头。父亲一死,又觉得父亲大树在,日子百般好,现在忽忽然倒掉,想起父亲在日的好,又不忍心丢弃了。我不丢,其他人吃粮不管事,所以日子如水,旧物依然。
父亲在世,横个声称传子孙传囡度西,直到临死才改口“呒啥传”。我之所以不丢,我相信老只脚色倌在天有灵,看看他横要传竖一声号称传子孙的东西,能千儿百年不朽下去?老早小时候读书,老师告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自忖,而今年纪活了五十又五,在这中间,自己扯着耳朵拼命往老师教导的方向靠拢。然而事与愿违,发现反而离老师的教导的目标值越活越远,为什么会这样子,臭皮囊想破头皮想不通,只好不想,还是留给来世的玲珑皮囊去想罢。要想搞清楚这类宏大的问题,唯一的条件是臭皮囊速朽,以便给后起的小玲珑让路。
自己也不曾想到过,活着活着会活成笑话。不要说“有益于人民”,就是有益于自己的事,也没做一件。在随波逐流的岁月里,活成了令周围所有人讨厌的货色,沦为纯粹的造粪机。一事无成两鬓斑,但求早死早超生。父亲啥样都要传子孙,无非是希望自己留名“钱”史。我的人生观正好相反,希望死后第二天就把我忘记,永远不再被人提起。古诗里有“燕过水无痕”一句,我与人世的关系,就希望这个样子。阒迹无形、阒迹无影、阒迹无声。
二 铰刀
铰刀就是铡刀。铰刀是带有口语话一点,严格书面语应该是铡刀。样子就是包公案里电视里看到的那般,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一个铡人头一个绞猪草,作为喂猪的食料。电视里放出来看到包公的龙头铡狗头铡,做得牢壮结实,架子上龙腾虎跃,张牙舞爪,透着皇权的凌厉与威势。而农家的铡刀架子,就没有那么臭讲究了。整个铡刀架子就像一只长条凳子的改版,四条大长腿支楞起一只窄面,铡刀就按在窄面上,显得土里土气。
这把铡刀,与我的生命发生过小小的也或许可以讲大大的关联。我一直记得一个场景,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这个场景在我回忆里依然清晰。76年寒头天,呼啸的北风从老屋的院堂门缝里钻进来,我裹着父亲的棉大衣,在昏暗的洋油盏底下,昏昏欲睡。偶尔睁眼看着父亲不紧不慢地绞着番芋藤,准备明天的猪食。父亲那时还在做小队里的猪倌,负责小队里4条壮猪和一头猪娘。只见平时麻利的父亲,当时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忽然一阵“吱嘎”声,伴随一阵冷气飘进来,寿材板做的院堂门被推开了,娘进屋,对父亲说,“老伯只弗来三哉”。父亲马上跳起来,跨过包围着他的草蓝和番芋藤,一边急切地问娘,“恩断气哉,恩断气哉?”父亲走到门口,想到了什么似的,返身回来,掖了掖我的大衣,抱起我就往门外走,把我撂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扫平日里嘻皮笑脸的态度,脸色凝重地告诫我,要我小手捉牢座垫,双脚奔开,他要骑快快哉。
那一晚,董浜老公公咽气了,父亲当年失去他的老伯只,就像今天我失去父亲一样,大树倒了,心里好几年空落落,像心头少了一块肉。从这个寒当开始,从此我有了记忆。大公公死后,我家就拆了一半老屋,移了一个宅基影子,搬到后面的空地上,建造了属于自家的独门独户的平房。房子造好以后,父亲不止一次叹息着说,“要是老伯只活着几乎好,接他来住几天”。父亲叹息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是啊,在父亲的立场上,爹好娘好不如老伯只好。如果没有老伯只出面,他也不可能拆半座老屋,我的好公好婆更不可能答应作为小儿子的父亲移到屋后上好的空地,独立造房。分家叫开枝散叶,这个开枝散叶在以前是大佬佬的大事,要总家宗亲全部点头,“三对面六对头”全无异议,才算通过。我父亲本身是小儿子,势单力孤,如果没有老公公的声望帮他撑腰,现在我们家只会落在后北三间。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里,长子长房,在承继宗族遗产方面,有很大优先权。如果按正常途径,现在我家位置就落在下丘势。这个居住环境,十分重要。先圣说“居移气养移体”。先不要说风水,就是宅基地地势高低,接受日照的敞阳程度,就影响人的一生,甚至影响几代人。所以父亲的“老伯只”,对我家恩重如山,于我家犹如神灵般的存在。他本人没有嫡亲子嗣,视父亲这个小侄子如亲儿子,所以死了这么多年,父亲在世时常常提及、念念不忘。受父亲影响,大公公的音容笑貌,在我记忆里栩栩如生。
父亲一生,做了两件英明的事,一件就是搬出老屋造平房单过,挣了个好宅基;另外一件,嘿嘿,就是装头装脚,造了我这个不成器的龙种。
三 河泥畚箕
挑河泥畚箕现在就放在围墙垴头上,也不知放了多少年了,反正一二十年不止了。我是看着不顺眼,早就想把它拿下来扔掉,但一来有鉴于铡刀三番五次地父亲把它捡回来,我怕伤父亲的心,更觉得犯不着跟他怄气,在他死前没有动弹,他死后,我好像缺了血气方刚那一股子生活的劲道,生活的热情被什么东西抽空了,懒休休不想动,一拖再拖,旧么事没丢掉,反而木匠秀才新增加了些贱文字。
“雄鸡一唱天下白”,雄鸡司晨,代表了一股雄壮高昂的气势。雄鸡昂着头每唤一声,总要抖嗦一下鸡头上的红环,“当红”就是这意思。在乡下,也俗谓“出环头”。父亲要强,用父亲原话是“咬臧”,这个“臧”是显摆。尽管父亲整个人体格不阔大,人群中只能属中等,但身上的犍子肉一块是一块,父亲常常引以为傲的,是在建造杨塘闸时,五六百斤的洋龙管子一肩挑,当时大队的青壮劳力都在建闸现场,父亲独个儿挑起来,看得大家瞠目结舌,力压群雄,引来赞誉无数。直到我成年,也还听到有人赞誉当年父亲的壮举,翘着大拇指说,“定根,不得了”。父亲真名不是“定”字,之所以把真名发音成“定根”,因为称呼父亲的人是落脚在这儿的插青,外地口音有些野。从他嘴里叫出来的父亲的名字,出人意料地极具戏剧效果。父亲也乐意这样歪打正着的叫他。日常当中,一个不经意的意外,传递出敲金戛玉的气象,一刹那的意外成为美丽的永久。
父亲咬臧,他说,十八九岁就开始抽烟,开始在队里挑担、传担。父亲讲了一件记忆犹新的事,和河泥畚箕有关。父亲虽然健壮,但个头不高,夏天挑河泥肥田,和老队长传担子,老队长正当盛年,而且高过父亲半个肩。老队长嘴里叼了支烟,悠悠地一个转身,和父亲错肩之时,趁着动作的惯性,打着转转的担子,就滑落到父亲的肩上。这一着看似轻松,但父亲初出茅庐,门槛不精,接担没有技巧,担子落肩,父亲吃重,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如果跌倒,那不但塌台面,弄不好还会闪了腰。可能记工分成色上也会有些上下。父亲说,我咬着牙硬力一挺,硬做挺住了,总算没有塌台。父亲恼火地说,大家都是总家亲,他给我吃添添,这一来兴,我认得余(他)。
上面,父亲提到抽烟,我是理解的,用一个社会上的说法,就是“出道”。一个青年,从少年过渡到青年,最大的认证,就是有人开明开亮在公开场合传烟给你。我学木匠那会,只能避着师傅我们几个小徒弟互相偷偷地抽,要直到台条椅凳、箱笼橱柜差不多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师傅才会请烟给你。这是给你莫大的荣誉,比今天博士论文通过导师的认证更要金贵。师傅给你请烟,是说明你的技艺在同业之间得到了认可,师傅一请烟,师兄师弟无不翕从,从此,别人也会尊称你一声“老师傅”了。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抽烟,从生理角度来讲,是你从青年步入了成年;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你脱离了学徒的身份,师傅也不再对你负责,好比驳船断缆,从此你得自己掌握航向。从父亲到我,我们这世代人的人生,都是从抽烟开始的,才算正式进入社会。
哦,忘了说,师傅请烟,也不全是好事,你接过师傅的烟后,就得回家准备谢师宴了。嗳,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普通家庭,又如何载得动几多人情几多愁,如果家境好,又何必来学手艺呢。而且在学徒时期,逢年过节,多少都要给师傅家准备点礼数。好在社会风气开放以后,手艺行当一些刻薄古板的规矩,多有松动,谢师宴可以推迟个一年半载,多数人家也会把谢师宴和儿子的定亲宴合并一起办的。
四 缸箦
方言当中,大多有音无字,今天这个“箦”字,常熟东乡土音介于“责”和“热”之间,就像把衬衫衣领竖起来,这个动作就是那字的发音,我在此用“箦”,取意近,我看网上也有叫“晒簟”、“晒笤”的。夏天,一大缸的麦子拿出去,摊开来晒。老早的泥土地晒场,麦子必须均匀地摊开在竹篾做的缸箦上,缸箦,类似于我们现在夏天睡的竹篾席。
连续几个好老太阳晒下来,抬出去一缸的麦子,等麦子吸干了水分,短时间内会变蓬松,傍晚收场,颗粒归缸会发现原先的缸里装不下来,这时,就得拿狭长的缸箦囤在缸口的四边沿,使麦粒不致外溢,洒落一地,等几个黄昏过后,它自然会落趸下去。这里,箦在缸口这条狭长的缸箦,叫茓子。吃喜酒,有毛手毛脚小青年帮老伯伯倒酒,手头不知轻重,倒得杯口杯沿一塌糊涂,这时候老伯伯就会说,“好哉,不要倒哉,浦出来要贴一根箦条囤一圈哉”。
16年端午前,我去篾作匠那里,想定做一条篾席,一尺六的,他开价350,说可以落低点。尽管我知道现在人工物料都涨,但仍超出了我预期。缸箦和篾席一样,都是竹篾片打作的。所不同的,篾席用的竹篾片狭而薄,缸箦的竹篾片宽一点,相对,也厚实一点。你不要看这个“一点”,我们的儿童时代是伴随着体力劳动成长起来的,夏天的时候,大人差使你把篾席拿出来,床上要换季了。你拿席子毫不费力,但拿同样一条缸箦,可能要费尽九牛二虎,关键就在“一点”上。篾席是细作,缸箦是粗作。
学过机械的都知道,人的头发丝,大致分七丝。做过金属精加工的有知道德国人把这分的更细。在过去师承关系谨严的时候,训练出来的民间匠人绝大多数都有一二手绝活。据说当年,有篾匠凭一把作刀,能劈出二丝的篾片。当然,时代发展了,现在多用劈篾机矫厚薄,省力省事省时。科技是个好东西,影响着人类的处境。科技在发展,世情在变化,人,就得与时俱进。
一根竹子,戕好篾片的宽度,打作篾席的,要窄一些,跟藤椅上的藤差不多宽。劈篾片,由表及里,做篾席的,只能用头黄二黄两刀,取新篁的韧劲,也使将来不容易产生虫蛀。缸箦则不须要那么讲究啦,二黄下去劈得到肉头的地方皆可以用,厚一点薄一点也无所谓,常熟人口中的所谓厚薄眼上眼下,差不多就可以啦。乡下儿童的成长也在这眼上眼下的间歇里上年不襻下年,夏天的时候拿得动篾席拿不动缸箦的小正太,吃了个年夜饭,腿肚子发粗手膀子发圆,第二年开春,就能力鼎山石了,少年人的力气,节节长。
可惜,我们现在缺了一门叫语意学的课程,中国式语言常常是花非花月非月的让人糊涂,指东而实西。在常熟东乡的语境里,劈篾片也称“劈篾头”,讲某人跟某人劈篾头,意指某跟某过不去,两个人在闹别扭甚至开始闹瓣。你看有意思吧,字面表述跟实际指陈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这点上看,是不是表明汉语言的博大!抑或是常熟先民对语意学玩的花样。
伍 板凳
小时候,跑过去到老屋里去跟好公睡,在好公床横头的墙上,老破老破沾满了蜘蛛网的旧帆布袋里,装着一把“大刀王五”那样的大刀,不过刀架子是由粗铁丝缠绕而成,上面挤挤麻麻,排满了清朝时期的铜钿,我看着新奇,就发嗲,缠着好公要拿来玩。那时人小,哪里懂得大人的心思,只好像好公略一迟疑,就随我了。而我,也只此玩了一个黄昏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宝货了。
感觉这个宝货凭空而来,又凭空消失了。
世界上没有凭空的东西,是凭空,必然带有某种神谕。好公84年先死,好婆直到98年,才跑忒,待两老全部动身,我也没能在他们身后,再看见过那把铜钿大刀。曾经在父子空档时,跟父亲提起过这事。只见父亲一口粗气喷出来,“你好公好婆早就塞给大老兄家了”。从父亲郁郁不平的口气里,我才实实在在感觉到长房长孙优先权的力量。总家传下来的家当,不是像电视上那样一家人和和气气均分一份,而是在日常操作当中,你要够精明,要够会拍马屁,把两位老大人糊弄得团团转,在光洁的表面相背后,手要像龙罩手那样摊开,“得家当得家当”,暗底里的才是得家当;开明开亮那叫分家当。这就是俗称的两面光,既得了便宜又讨得了乖。人生境界在为己,人不为己美如画,美如画来天诛灭,一心为己天地宽。
直到好婆死,我父亲熬不住,也伸了一次长手,去好婆老屋把一层木梯,二只老板凳拿回了家。父亲直筒子脾气,爷娘说啥是啥,这个梯子和凳子,也是姑母来撺掇只父亲,父亲才一个灵醒,不然,父亲只会愤愤不平,发发牢骚,半点不会小算盘。其实,父亲从爷娘那里把仅剩下的一点拿回来,也是平衡一下这些年跟老兄家吃了无数暗亏的心绪,梯子凳子,现在也没多大用场了。
前年冷天御寒,我生了个炉子,那只小一点的凳子被我丢到火膛里,大一点的丢进去了,我像感觉到了什么,又即刻一把拎了出来,总算是火口余生。这是一只及其普通的板凳,我也不知怎么灵光一闪,不舍得因为用来烘火而烧掉。细细地拿起来翻看了一下,才发现是个骨灰级的古董。凳面是老榆树,从木纹来看,是一棵不大的榆树的根部,凳面看上去厚实,但底面有一个大大的瓢虫洞,单从凳面说,有了这个瓢虫洞,再怎么榆树面也成了不拾流品,没多大价值了。器具在乎品相,而品相在乎没有瑕疵。
我为什么火中取栗丢了又把它捡回来,想想多半是惜材。祖宗如果有灵,我想会向我翘个大拇指。凳子的四条腿尽管也是榆树,但支撑在地上,长年累月,现在到处是水泥地面,可是老早统统是泥土地面,这只凳也不知道传有多少代了,泥土地上的湿气侵蚀的腿底只有筷子样一点芯芯支撑着地面,你想,新做的上好的榆树凳脚,虽然可能有白标可能有虫蛀坏道,但地面湿气能把凳脚腐蚀掉,这是需要多少日蚀月腐的积累啊,所以可以不夸张的估计,这只凳子没有两百年也最起码一百年。
岁岁年年相同凳,年年岁岁不同人。一轮二轮……也无处考证这只凳子传了几代人了,而今这只凳子流落到我手上,有无数感而慨之在胸中。想想,也看父亲帮我学了木匠,我就生一把好手,把这个榆树凳面利用一下。这个,不动手不注意,一动手却被小小的考验了一下,从凳面上蜕下糟朽了的凳脚,才发现凳面的斜眼,两头做有三角倒雀,在凳面,亦称斜雀,这是我做了几十年木匠,还第一次遇到,我们现在图省事,都是做直平榫,就是卯眼凿的的角四方,这样直接敲进去省事多了。好在天生一个小木匠,手艺长青文长东,这点小伎俩是远不足以难倒我的。
六 连只
今天写的家什,“连”不是这个“连”,“只”不是这个“只”,但常熟宁看得懂,看不懂的我用另一个词表述,“苇席”,芦苇做的席子。我粗略翻了翻周立波《山乡巨变》、《小二黑结婚》等,也没查出个名堂。依字面意思,私淑里我更愿意以“簾子”来指代“连只”。可是“簾”通“帘”,用簾子簾席会被误认为是横隔在皇帝和西太后中间的垂帘听政,我不想让人有这个误会。这道细篾美帛糊的帘子,遗害无穷。我是真心希望撤去各种有形无形的簾子,让天下康梁俱欢颜。
我学生意时,有一次师傅给了我钱,叫我去供销社竹木部买几卷毛簾。我想,啥个毛簾,但不敢问师傅,我卖了个乖,想,既然叫我去供销社,他们卖的人总归知道的。买了才知道,这是乡下建造简易房屋用的。用在瓦片底下替代芒砖,类似于今天建高速公路用的土工布,起隔离防水作用。这个毛簾,还有一个古老的作用,战死沙场的。大家多知道好男儿有马革裹尸的悲壮,但穷乡僻壤的人家根本连马革也没有,就只能买一卷毛簾裹尸,草草薄葬。芦席裹尸,史,诗,词,笔记小说,不乏其记。
看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多少先民使用的日常器具有很多都断代了,不见流传下来,但苇席——也就是常熟人口中的“连只”流传了下来。当然,一起流传下来的还有许多,但无疑苇席是具有顽强生命力中的一种。我在想,有顽强生命力,这句话没问题,听上去很好很正能量,但是否又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观念,生活环境,特别是劳动生产生活的方式上,几千年变化不大呢。我们看《浮生六记》,看《能静居日记》,都提及毛簾裹尸的窘迫,许多寒门甚至连薄殓简葬也做不到,令人唏嘘。在《古诗十九首》之中、乃至上溯《诗经》的场景中,字里行间的情与状、人与貌,与过去的百十来年前岂止略相似,可以说原始的朴茂毫无二致。社会几千年的停滞,生产生活没有变化,人们因循守旧,家用器具当然也无所变化。
在朋友家吃饭,刚好与他赵市长江边的老丈人同桌。他老丈人得知我是徐市人,感慨万千,说徐市好几十年没有去过了,那时大集体时经常去。我问他去做啥。他说卖连只。当时长江边有的是芦苇,生产队组织起来搞副业,做好了连只就摇船往内乡去卖。而徐市没有大江也没有大湖大河,没有大面积产芦苇的滩涂,又是高乡产棉大区,棉花从田里棉树上摘下来,晒干水分,而这个晒,就要动用到连只,因为棉区产量高,所以对连只的需求量也高。当时摇出来一船连只,一个生产队就包了,十分抢手。
话说回来,家用的连只,和毛簾不同,要精致很多。首先,一卷连只摊开来两米多,在精壮的芦苇中间,夹杂着细细的小青竹子,为整个连只起到骨骼支撑作用,使连只更牢固结实。而绞辫芦苇竹梗的麻绳,也透着金灿灿新篁的光泽。连外行的女娘客看了也觉得是上好的实在货。连只和篾席不同,连只间隙粗,有漏缝,晾晒东西透气性好。一卷连只整体分量轻,一般女娘子都拿得动。所以动到晒场,连只最实用。在过去,一条连只要用用一代人,好几十年用下来也不见坏。社会长久的停滞,造成了浓厚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弊端之一,就是小农思想影响下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协作,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一年到头,家家忙、人人忙、日日忙、时时刻刻忙,可悲的是代代忙,但饶是如此,请问社会的财富积累呢,你看到吗。
七 后记
父亲张口闭口常常一个“传”字挂在嘴边,本打算一路写下去,发泄发泻自己的怨气。锄头、铁耙、镰刀、匾子,也有故事写。开首写时鼓了一肚子的怨气,写着写着,想到父亲昨日的种种好,对比今日种种的冷,气慢慢消了。再反思自己,我好逸恶劳,只怨父亲不是书记,我没有恶少的本钱。再接着,遇到一个场景,使我一下子漏气了,转瞬干活的精神劲也崩溃掉了。
前阵子,搭紫藤花棚架的时候,下午17点天擦黑,但活儿半尼弗三,无法丢下工具就歇手,最后到18点过后天色断暗,我拖着药力不济的病体回到厨房间,又累又饿又渴,喉咙里一口疲惫的气鲠在那里不上不下,堵得人不想吃也吃不下,一个人瘫倒在椅子里,众人皆视作陌路。我人跌坐在椅子里,脑筋里想,父亲在,断断不会是这个腔三,他如果从田里回来,一点会说,“小东,歇吧,只有天亮呒夜日哉,明朝再来”。父亲的一句关怀,暖人心肠。我有个坏习惯,干活工具东丢西厾,即使我断暗歇工,父亲也会把我的工具收归好,拿进来码放整齐。
父亲在时,这类小意思我骨搭不着,觉得介类小动作父亲自然而然应该个哇。但是现在父亲不在了,我盛一碗中午的剩饭,舀开水吃了,再吃药,还要驻着拐杖打着手电去把外面散落的工具捡拾回来,可以说把洪荒之力也耗尽了。你说叫我怎能不念起父亲的好。一家人,父亲在,还能感觉到暖气。而我那好娘,有故事讲:30年前,我第一年结婚那个夏天,我,和隔壁的隔壁人家同时装了一台空调,当天晚上,隔壁的婶娘睡在隔壁的隔壁女人的空调间里,她们俩女娘家要好。接着第二天早上,婶娘看我好娘上河滩,喊娘说,“玉英玉英,我告诉嫩听,空调里真个舒服,比在仓库场上吹风凉适意交关,难怪家家都要装空调”。好娘说,“空调都是有铜钿人住个,无铜钿人嫑去望天鹅肉哉。我们做田里,这世人生是嫑去巴望啥空调弗空调”。一句话,婶娘噎得无话可说。而我在边上,听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知道这句话只是一半说给婶娘听,一半是笑话我这个“呒铜钿资本家”大手大脚。而三十年后的娘,田里回来放下三轮车,洗了个手端了饭碗拿了个小菜碗直冲空调里。院墙内院墙外,全都是田里带回来的碎草和泥土。我理解她年纪大了。但忍不住想,自己兴冲冲钻空调里,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所说腌渍话,把话说得太满,像门闩横在门当中,细风息息吹不进,这个用常熟土话讲就是“横门劲”。
回味来时路,半夜细想,父亲没有给我带来大吉大运,父亲的好是细碎的,日常当中见缝插针式的好,你粗心大意领会不到的好。要细细地瓣开来糅进去成面团,还原文字,可以写很多很多,书上说父爱的伟大,我不懂也不管伟大不伟大,我同父亲的感情,是合脚连膀,合筋连脊,我撅屁股,父亲知道拉什么屁的心有灵犀。无奈,人总归要死的,再融洽的父子也要分手,尘归尘土归土,阎王路上只能一人走。而娘看到父子不和,冷言冷语;看到父子同心相契,又怪声怪调。娘爱看父子间的笑话,常常骂:老赤棺材老牌位,你嗲儿子么你搭天梯给他。好娘信奉“棍棒头上出孝子”,和父亲在对待我的态度、方法上多有违拗。我背地里多次挑唆父亲跟娘离婚,可父亲总是说,“闹归闹,我们有老交情的”。他还把“老交情”三个字咬出来,拖出一个长长的尾音。劝我,凡事都忍忍,事情就过去了。父亲怎么也不上我的当。如今,我只得篡改一下李后主的《破阵子》,“最悲仓皇辞父日,好娘犹奏别离歌”,来形容父亲、娘、我,也为父亲的《食货志》划个句号。
202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