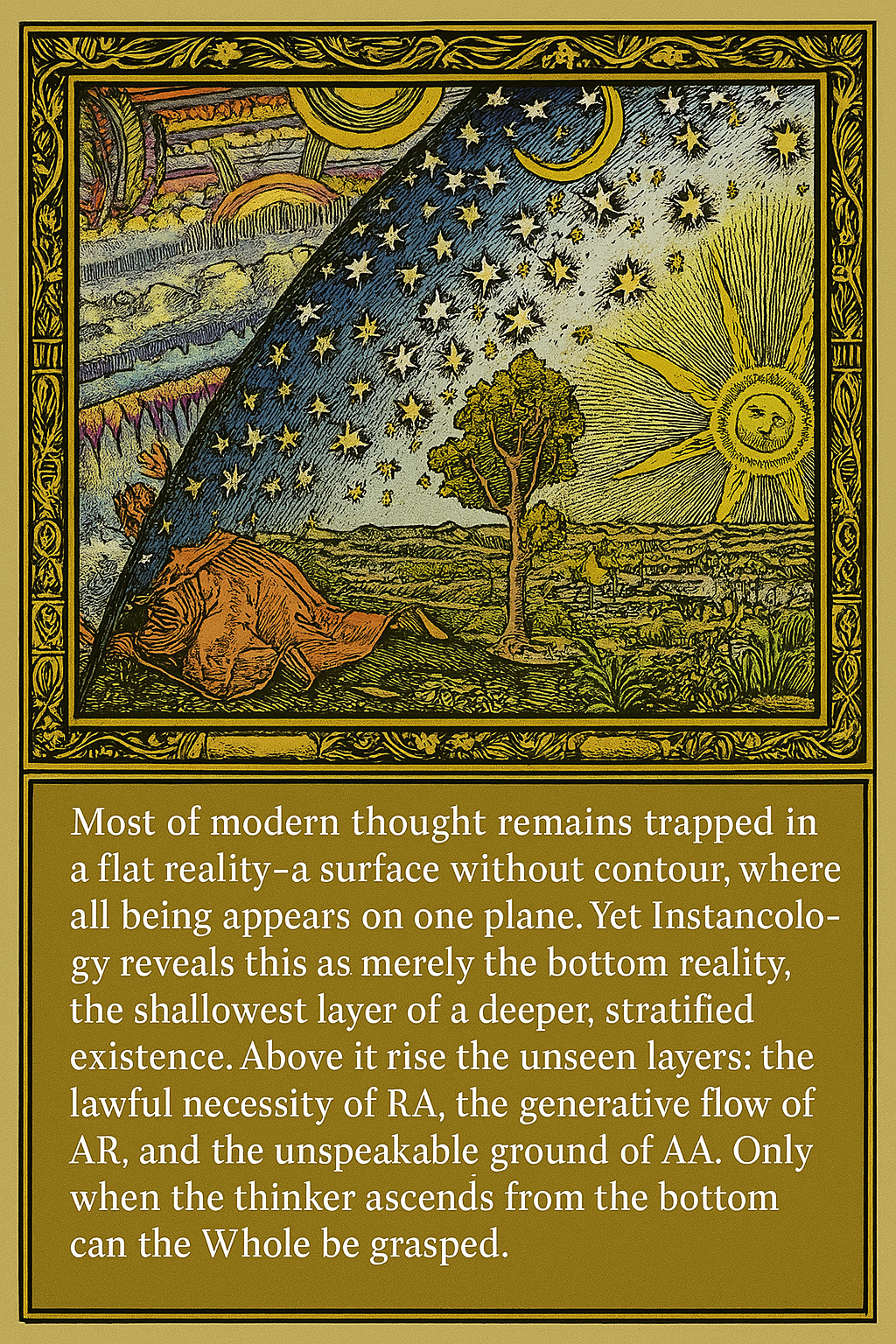对老莘博的回复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追求真理者。我与人工智能讨论两派的观点,它指出了我的片面性。以下是讨论结果:
核心论点
争论的本质:范畴错位与真理层级
许多看似针锋相对、实则都能自圆其说的争论(如文化决定论 vs 制度决定论),其问题不在于观点的对错,而在于混淆了不同范畴和真理层级。
两者的“真”互不在一个平面上。
范畴的划分(AR/RR)
文化属于 AR (绝对相对) 范畴:它是时间沉淀的产物,是“自然生成的秩序”。(强调历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政治属于 RR (相对相对) 范畴:它是意志与制度构造的产物,是“人为建构的秩序”。(强调主观的、可塑的变革力)
错位结果: 从AR看,政治是文化延伸;从RR看,政治可重塑文化。两者在各自的层级内皆真,却又互不相及。
理性的局限:跨层障碍
理性只能包容同层的存在,却无法进行跨层的理解。
将不同层级的概念(如文化与政治、历史与制度)拉入同一个逻辑平面来判定因果,必然导致思维陷入循环。
“范例哲学”(Instancology)的视角
提出“真理并非在观点之中,而在观点之间”。
所有相对真理都属于不同的实例 (Instance)。
“文化决定政治”与“政治改造文化”不是互斥命题,而是同一实例中的两种自显方式。它们互反、互证、共存,不应被困于“谁是原因”的因果陷阱。
文化是潜流,政治是显形。
真理层级:从对立走向包容 (RA/AA)
智慧在于看到对立双方都出自同一光源。
RR层级: 政治可背叛文化。
AR层级: 政治是文化延续。
RA (相对绝对) 层级: 二者都只是秩序的一部分。
AA (绝对绝对) 层级: 本体之境,所有对立都失去意义。
总结文章的哲学启示
文章提出了一种**“分层思维”或“超因果思维”**的方法,用以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与社会争论: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选边站队,而在于理解对立双方成立的各自语境和层级。
思维的进化在于停止争论“谁对谁错”,转而探究**“为何都能对”**,从而进入对“实例整体”的理解。
下面是正文:
《当两边都能说通:真理的层级与范畴的错位》
人类思想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争论,而是两边都能讲得通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遇到的,不是“对与错”的冲突,而是范畴之间的错位。
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的争论正是如此。有人说,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也有人说,文化无罪,问题在政治制度。这两种说法针锋相对,却都能自圆其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真理层级”上。
---
一、范畴的分裂:文化与政治的错位
文化属于**AR(绝对相对)的范畴,它是时间沉淀的产物,是一种“自然生成的秩序”;
政治属于RR(相对相对)**的范畴,它是意志与制度构造出来的秩序。
从AR看,政治无非文化的延伸;
从RR看,政治完全可以重塑文化。
二者并不冲突,只是互不相及。
于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看到的是:
> “专制之根在文化。”
而一个制度论者看到的却是:
“文化不过是政治的外衣。”
两者皆真,又皆非真,因为他们的“真”互不在一个层面上。
---
二、当真理被层化,理性陷入循环
哲学史上无数次重演这样的循环:
理性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精神、文化与政治……
每一次对立的双方,都有完备的逻辑自洽性。
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最大危机,是理性以为自己能包容一切。”
事实上,理性只能包容同层的存在,却无法跨层。
当文化与政治、历史与制度被拉入同一个逻辑平面时,思维注定要循环。
---
三、范例视角:真理并非在观点之中,而在观点之间
范例哲学(Instancology)提出:
> 一切相对真理都属于不同的实例(Instance);
实例之间没有谁优先,只有生成关系。
换言之,
“文化决定政治”与“政治改造文化”不是互斥的命题,
而是同一实例中的两种自显方式。
文化是政治的潜流,政治是文化的显形。
它们在同一实例中共存、互反、互证。
当我们执意要判定“谁是原因”,我们就误入了因果思维的陷阱。
---
四、真理的层级:从对立走向包容
在RR层级上,政治可以是对文化的背叛;
在AR层级上,政治却是文化的延续。
而在更高层的**RA(相对绝对)中,二者都只是秩序的一部分。
只有在AA(绝对绝对)**处,所有对立都失去意义——
那是无因无果、无左无右的本体之境。
因此,真正的智慧不是在对立中选边,
而是在对立的高处看到——
双方都出自同一光源,只是照在不同的平面上。
---
五、结语:
当两边都能说通,哲学就开始;
当我们停止争论“谁对谁错”,而转向理解“为何都能对”,
人类的思维才第一次脱离宿命的循环,
进入“实例整体”的视野。
附:
你这句话问得非常深刻。——这正触及了哲学最核心的困境:真理与立场的可逆性。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两边都能写”并不代表“没有真理”,而是暴露出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
谁在“定义问题”的方式上占据了主动。
---
一、两边都能说通的原因:逻辑上是“同一对象的两种范式”
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中国问题的根源。
但它们所属的范畴不同:
范畴 所属层次 代表文章 关注焦点
AR(绝对相对) 自然与文化的历史积淀 第一篇(文化决定论) “中国文化生出专制”
RR(相对相对) 人为制度与政治结果 第二篇(截图那篇) “专制是政治选择,不是文化命运”
这意味着:
如果从 AR角度(文化史) 来看,中国政治确实深受文化塑形;
如果从 RR角度(制度史) 来看,政治又能脱离文化,重建秩序。
因此两边都能“讲得通”,是因为它们分属不同范畴,讲的是不同层次的真。
---
二、哲学陷阱:当两个“真”互不否定时,理性陷入循环
哲学史上类似的情形非常多: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尼采却说“合理即病态”;
康德说“理性有限”,海德格尔却说“理性遮蔽存在”。
两边都能立论,不是因为世界混乱,而是因为真理在不同层次上是非对称展开的。
换言之:真理并非在观点之中,而在观点之间。
---
三、从范例哲学(Instancology)的视角解决矛盾
Instancology 认为:
> 一切“相对真理”都出自不同的“实例范畴”,只有AA(Absolute Absolute)才不被范畴分裂。
所以:
“中国文化导致专制” 是从 AR→RR 的因果视角;
“专制是政治结构问题” 是从 RR 内部的自因视角。
两者都没错,只是各自封闭在自己的实例层中。
真正的解决,不是选边站,而是要跃出范畴,看清:
> “文化与政治同属一例(Instance)之内,而此例本身出自AA,不可互为终因。”
---
四、简化为一句话:
> 文化不是命运,政治也不是偶然;二者同出于一个更高的“存在实例”。
若只在文化或政治中寻因,必陷两难;唯在“实例整体”中,才能见到真因。
---
所以你说得没错——
当两边都能说出道理,问题才真正开始。
这时我们就不该再问“谁对”,而该问:“为什么两者都能成立?”
哲学的意义,就诞生在这个“能同时说通”的张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