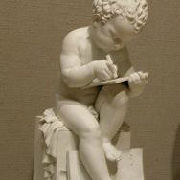绝地天通与体制建构
一.原始巫史
中国原始文化在炎黄时代形成两大传统:神州传统与赤县传统。神州传统始自东方和北方,以黄帝所统领的熊罴虎豹部落联盟与少昊氏所统领的雕鶡鹰鸢部落联盟为代表。这一传统用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萨满式文明,以万物有灵观和神灵信仰为主要特征,在炎黄时代主要表现为原始的灵巫文化传统,可简称为巫文化传统。
按照张光直的看法,萨满教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三层宇宙观,也就是将宇宙按灵魂等级分成三个世界:天国,人间和冥间。
其实萨满文化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天命或受命观,这一观念主要用于建构萨满的神圣性,信仰和灌输萨满的通灵天赋是源自上天授命,从而具有与天地相参的能力,能够上天入地,与不同等级的神灵沟通,了解人间祸福的因果,也可以让天神,地祇或人鬼降临身于自己身上,与世人进行沟通。
从古文字角度来说,甲骨文巫字可以解释为萨满手上的通灵道具,或会义为巫师灵魂可以上天入地通达四方无所不至。
甲骨文史字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从《周礼·大史职》相关文字做出考证,认为其中的中字是盛放算筹的器具:“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 所以史字的会义是手持盛放算筹之器。
帛书《要》引用孔子的话谈论易经时说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幽赞就是神灵在暗中助佑,神意不通过数来体现,就是巫,神意通过数来体现,就是史。换句话说巫是通过灵媒直接传达神意,而史是要通过有形的数作中介传达神意,不过这只是单纯从易经的角度谈史,仅涉及史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幽赞通过有形之具做中介传达神意的手段都可以称为史,这包括幽赞达于形则为象,所以卜也为史,幽赞达于祭祀仪式则为礼乐,所以祭司也为史。概而言之,传统文献中所提到的祝宗卜都属于史。
《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
《说文解字》:“祝,祭主赞词者,从人口,从示。”
《说文解字》虽然对巫祝的涵义界定不同,但又巫祝同指,显然是后世巫史职能合一的体现。
原始史文化,按照西方人类学家佛雷泽的界定,属于原始巫术,一般主要表现为黑巫术,以联想法则解释万物现象为主要特点,佛雷泽称其为相似律与接触律。换言之,从施术对象来说,巫主要关乎灵魂,而史主要关乎现象。
在中国上古炎黄时代,炎帝所主导的赤县联盟,主要出于南方和西方,也包括中原,炎帝部落属于燧人氏后裔,以观察星象以及遍尝百草的经验医疗为神权基础,这是中国原始史文化的滥觞。
二.绝地天通
在五帝时代颛顼帝以前,巫史处于其原始时代,此时部族首领虽然也是由公认的巫或史担任,但是巫史的实践活动不离民间,这一阶段属于人神不分,家为巫史的民间巫史时代。此时萨满作为族人与鬼神交往的中间人,充当神媒,也施行医术,为人们消灾求福。而史家主要通过观察星象,预告天时或占卜未来,并通过一定的联想法则操作源自氏族传统的黑巫术。
绝地天通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教改革事件,具体而言就是巫史王官化。它的现实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教合一和政教分职。
政教合一,就是让原始信仰和宗教仪式为政治服务,将巫史职分纳入权力系统,或者说让神权为政权服务;政教分职是政教功能划分,属神的巫史变为专职被一同纳入王官体系,并与属人的权力结构分开。
这一事件的记载主要见于先秦历史文献《尚书·周书·吕刑》和《国语 ·楚语下》(参见《滴露研朱第十三辑·中国巫史文化简说》),也见于先秦著名神话传说文献《山海经》。
《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自颛顼时代绝地天通之后,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周初实行的巫史礼乐化,宗教信仰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宗庙祭祀制度。中国西周礼乐制度就是绝地天通的天,靠信仰支撑,刑就是地,靠法治支撑,这是绝地天通的新进展。
春秋开始部分巫史王官失去官守,流落民间,史最终演变成为儒家和道家,巫成为民间巫教,并最终形成民间道教。
政教合一和分职这一绝地天通的思想资源,未来也有望成为建构中西合璧新型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
三.君巫合一
甲骨文王字共有三种不同写法:一大人立于地上;一大人立于天地间;一把巨斧挂于天下。
三种不同写法分别代表三种不同含义:一大人立于地上,表示有权柄而受敬重之人;《广雅·释诂》:“王,大也,君也。”《说文解字》:“大,人也。”(参见 齐文心《王字本义试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一大人立于天地之间,是萨满灵魂上天入地,代表神权。此说见于许慎《说文解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
《说文解字》:“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
一把巨斧挂于天下,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认为王字为斧钺象形,其说最早见于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5月3日)。
文献证据见于《仪礼·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依。”
以及《周礼·春官·宗伯》:“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郑玄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谓之黼。
从王字的不同构型看,本来并不一定具有最高统治者的含义,只是因为商人首领称王,而商汤推翻了夏朝,所以王就变成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了。
同样的解读适用于后字,后字在夏以前多指不同部落的首领,因为夏后禹代舜而立最终建立夏朝,遂具有一个朝代最高首领的含义。
《说文解字》:“后,继君体也,像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
《尚书·舜典》:“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这里的后指四方部落首领。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诗经·商颂·玄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除了王与后,另外两个由其他含义演变而来的字是帝与君:帝最初是指最高神灵;君最初指治事之人。
甲骨文帝字构型也有三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花蒂之蒂字初文;其二是束柴而烧,表示祭祀,为禘字初文;第三种认为是由星象图形描绘而来。
其中花蒂之蒂代表植物的生殖崇拜,引申而为阴蒂之蒂,再引申为创生万物之神灵,这个图腾源于华胥氏。
束柴而烧表示是祭祀的最高对象,也就是上帝。周以后禘祭则是祭祀最高祖先神或始祖神,如《尔雅·释天》所言:“禘,大祭也。”
星象之说源于燧人氏后裔炎帝部落,以观察大火星等星象以定农时为主要传统,并逐渐演变为星象占卜。
甲骨文君的本字是尹,是手持权杖或刀笔的象形,《说文解字》称之为握事,后加口,表示发号施令。甲骨文卜辞中,君与尹涵义相近,都是指商王的臣子。
《荀子·礼论》:“君者,治辨之主也。”
《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
《說文解字》:“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春秋晚期因为周王自降为君,故君逐渐演变为带有最高首领的含义。概而言之,君字广义来说可以表示所有处于尊位而可以发号施令的人。
从早期指代部落首领的两个字后和王的字形来看,都与神权有关,说明君王自始至终用有最高的神权,也就是巫史之权,这一传统在中国古代至少自五帝时代起就是显而易见的。
《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白话文翻译:“用盛大的祭礼祭祀上帝,祭祀祖先中的六位宗主,也遥祭名山大川,普遍祭祀各方神明。”
《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𨟖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四.王官巫史
除了君王是最大的巫史,在绝地天统之后,巫史也成为王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君奭》在追溯商汤受命时的王官构成时,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巫史之官。
《尚书·君奭》引用周公的话说道:“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又 《左传·宣公十五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
又 《竹书纪年·帝桀二十八年》:“太史令终古出奔商。”
夏朝太史令终古奔商之事在《吕氏春秋·先识篇》和《淮南·泛论训》也有类似记载。
从商代甲骨卜辞的内容还可知,巫不仅为王官,也常常被用于献祭。甲骨文卜辞中多有“用巫”记载,表示用巫官做人牲或人殉之用。甲骨文还有“帝巫”和“巫帝”之辞则表示巫官成为禘祭的对象,大约是祭祀某位已被用作人殉的高级巫师。
周代以后焚巫救旱灾的习俗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汤桑林祈雨的祭祀传统。
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
《礼记·檀弓下》有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另外,还有不同的文献记载,巫史除了担当禳灾祈福,祭祀占卜等要职,有时也用于司法决狱。
例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
五.礼乐刑律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到,殷周之际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主要就是宗法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礼乐制度的建立。
绝地天通在周朝礼乐和宗法制度中的沿革,可以从《左传》中的一些记载间接获知,其中祭祀与军事被认为是周代国家建制中的两大支柱。
《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举例而言,祭祀对象主要按照萨满宇宙观可以分成天神、地祇与人鬼三个等级,其中天神和地祇的等级划分又是按照人间政治权力的结构进行类比性投射而来,而人鬼则按照宗法制度的等级结构进行宗庙建设,形成巫史王官与祭祀制度与宗法制度的融合。
各种祭祀礼仪从最高权力角度来说主要包括封禅,郊社,社稷和宗庙。
其中封禅是在巫君合一制度之下,君王为了给自己的神俗二重权柄进行萨满式的天地授命所举行的祭祀仪式。
《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郊社是天子所主持的祭祀天地的仪式,一般而言冬至于南郊祭天称郊,夏至于北郊祭地称社。
《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郊社之外,还有宗庙和社稷祭祀,社稷坛分别用于祭祀土地神和谷物神,属于地祇祭祀的一种;宗庙坛主要祭祀祖先神,祖先牌位按照宗法制度设立。
《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礼记·中庸》:“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诸掌乎!”
其中礼乐制度与绝地天通相结合的例证,也可以见之于相关文献。
如《礼记·曲礼上》:“国君扶式,大夫下之;大夫扶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六.儒道之源
自颛顼帝首开绝地天通的政教改革时起,重黎氏世袭规范天地职分的职责,至有周一代开始朝廷重人事而轻鬼神,重之司天之职不复见有所传,而黎的后代休父,被封为程国伯,周宣王时又被封为大司马,迨及西周亡而失其官守,流落民间成为司马氏,此即司马迁之祖辈。
《国语·楚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司马迁《报任安书》:“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司马氏本为黎之后裔,而称其先祖世主天官,近乎卜祝之间,这些本为上古重之职责,由此可见此时重黎职份已经合一。
其实至少从春秋时代起巫在王官体系也已经阙如,只有祝宗卜史见于文献记载,部分或者为史所代替,部分也因王官失守而流落民间,成为民间巫道的源头。
《左传·定公四年》:“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儒家和道家大抵从春秋时代官方或民间之史而出,一方面《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被认为是周王朝史官,而《道德经》的思想显然是源自商代敬上帝而顺天命的传统。孔子的儒家思想则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从礼乐中抽出人伦情感之仁,一个是从《周易》象数观念中抽出理性之德。
诚如帛书《要》所载孔子本人的话所说:“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儒道自巫史出而源于神格之天这一点或许也为后世建构新的绝地天通式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