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的复苏与民族的漂泊:冯知明先生《四十岁的一对指甲》对谈录
时间:2023年3月3日
地点:北京·南京——香山南苑/紫金山麓的隔空对话
1.引言: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

詹乃德:云兄,很荣幸能够接受您的邀请,为您的长篇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撰写书评。我在2020年就已初读,但直到今年重读数遍,才敢发表一些粗浅的见解。这部作品虽非巨著,篇幅三十万字,但其磅礴的气势、丰富的内容以及跨越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都使我感到震撼。它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面透视镜,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与个体的精神变迁,尤其是它以荆楚文化为根基,对“巫”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基因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作为一名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我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与文化记忆。
云梦泽人:詹博士的见解深邃,令我受益匪浅。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不过是记录个人和时代的命运,没想到您能从如此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进行解读,这确实提升了这部作品的高度。感谢您拨冗阅读。您刚才提到的“巫”,恰恰是这部小说的起点。小说主人公“敏”的原型,正是我的童年经历,而他外婆“贞之”的原型,便是我的外婆——一位法力高强的“大巫婆”。在那个纯真却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童年,我亲历过许多难以用现代科学解释的“神迹”,例如书中所描写的“两巫斗法,十里法场结界”,这些都并非凭空想象。正是这些亲身经历,让我感到“巫”不仅是远古的传说,它在我的故乡、在荆楚大地,始终与人类生生不息,即使是在“大灭四旧”的红色运动中,也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我对故乡和外婆记忆的一次文学“招魂”。
2.黄河畔的“理性”与长江边的“神迹”:中原与荆楚文明对巫文化的两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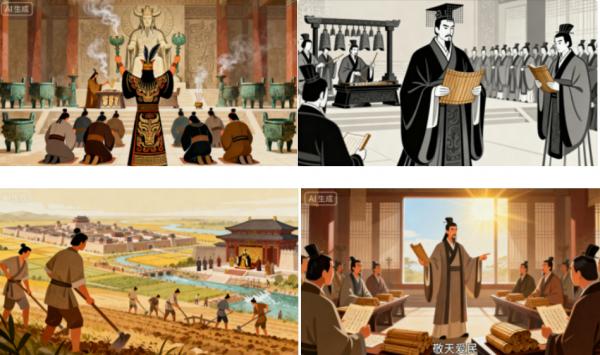
詹乃德:云兄的亲身经历,正是我们探讨“巫”文化的最佳切入点。这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源头,探究中国南北方文化对“巫”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看,人类最初对世界的认知普遍源于“巫”,这一点在殷商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礼记·表记》中便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记载,鬼神祭祀与崇拜贯穿整个上古时代,巫师在社会中拥有极高的地位,是沟通神灵的核心媒介。
然而,当历史的指针拨向周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朝兴起后,黄河流域开始采用一套偏向理性的思想体系,即以“天命观”为核心的“礼乐文明”,来逐渐疏远原先的鬼神崇拜。这套思想体系强调“敬天爱民”,将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统治者的“德”之上,而非巫术与祭祀。这是一种从“神本”到“人本”的理性化转向,旨在建立一个更为可控、以人文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由此,巫文化在周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非主流的、应该被批判的对象。
云梦泽人:我完全认同詹博士的观点。这种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楚国所接纳。楚人从血统上就自认高贵,屈原《离骚》开篇便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暗示楚国贵族是黄帝的后裔,无需遵从周朝的礼制。更重要的是,楚文化从一开始就“掺杂诸多‘巫’术”,并将其视为核心组成部分。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更深深地根植于文化基因之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楚辞》,从屈原到宋玉,这些文学作品中无不充斥着大量关于“魂魄鬼神”的描绘,这正是荆楚文化与自然、与鬼神世界保持着紧密、非理性联结的体现。
詹乃德:事实上,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不仅在于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地理与生态的塑造。黄河流域气候温润,资源丰富,但人口密集,因此内外部对此区域的争夺激烈,面临着严酷的权力挑战,以及频繁的洪水灾难,促使人们发展出以集权、秩序、农耕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周朝的“礼乐”正是这种模式的集中体现。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来应对不可预测的自然力量。而长江流域则不然,气候“湿热”,物产丰富,原始的自然崇拜在这里更容易存留。这种环境孕育了更具想象力、更感性、更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周人批判“巫”,是为了建立一个可控的人间秩序;而楚人接纳“巫”,则是其原始生态、自由奔放精神的自然流露。因此,周文化与楚文化的“对抗与冲突”不仅仅是思想之争,更是一场生存模式与文明主导权之争。
3.历史的演进与巫的嬗变:从殷商原始巫文化到民国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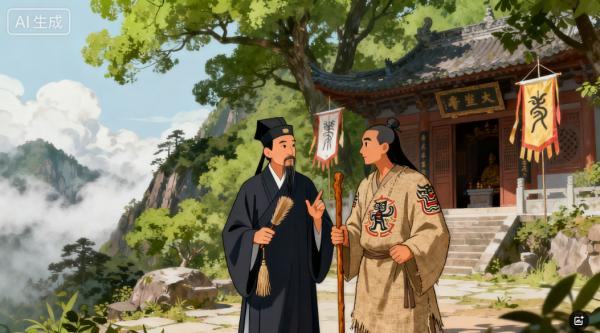
云梦泽人:这种差异,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秦王朝虽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并未能在思想文化上真正统一南北。楚地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外,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尽管中原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断“排巫”,但巫文化并未真正消亡,反而从显性的政治中心,退居到隐性的文化边缘,即广大的民间社会。它不再是国家大典,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死嫁娶、耕种渔猎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人口的南迁,巫文化与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和本土信仰“杂糅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信仰体系。
詹乃德:云兄的观点非常精辟,这正是巫文化的“潜流”与民间社会的韧性所在。它并未被同化,而是在与其它信仰的交融中,不断提供新的本地化元素,使其得以继续繁衍。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近代革命的到来,巫文化被简单地定义为“封建迷信”而遭到彻底的“洗礼”和“批斗”。然而,诡异的是,云兄在书中描述的“大灭四旧”时期,人们内心深处“对‘巫’的信仰甚至迷恋并没有被剪除”。它只是暂时失去了外在的表达形式。
云梦泽人:是的,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当“红色运动”结束,过去被顶礼膜拜的“巨神”轰然坍塌后,民间的神灵便“纷纷冒出”,甚至演变为对“伟大人物的崇拜”和改革开放后的“对金钱的崇拜”。这正是我所认为的,人们内在的、对精神图腾的崇拜需求,并不会因为外在的口号而被消灭,它只会寻找新的对象,或以另一种面目示人。这揭示了现代性在解决人类精神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败。
4.精神的流亡与现代人的回归:迷惘一代的心灵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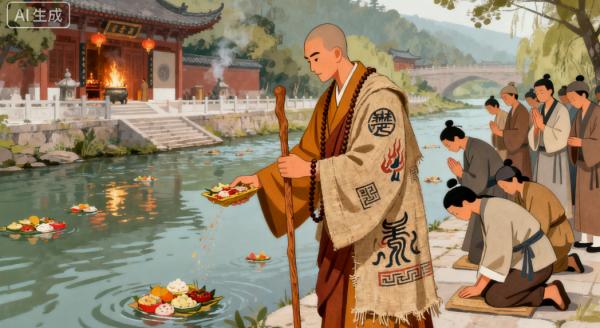
云梦泽人:这也正是主人公“敏”悲剧的根源。他原本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却在一夜之间被打入“黑线人物”的深渊,被迫退学回家。他曾为了与“封资修”决裂而砍伐了家中的风水古树,导致村中鸡猪发瘟,独子溺水而亡,被烙上“害人终害己”的印记。这个曾在台上作批斗发言的学生会主席,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他试图挣脱过去,将自己“装扮得很现代”,但他的精神实质依然是“外婆贞之为他构架的”。他无法回到故乡,也无法真正融入现代都市,成为了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不断“漂泊与流浪”,失去了“精神故乡”的典型代表。
詹乃德:敏的悲剧并非个体的偶然,而是整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集体“精神流亡”的微观再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政治挂帅”的坍塌,思想的混乱时期。而他与书中其他角色的互动,也构成了他精神困境的种种画面。他的妻子瑾,一位研究耳朵和调试听力的科学家,试图用科学的“规范”来重塑他的生活,但最终失败,不得不刊登“出租丈夫启事”。这象征着纯粹的理性与规范,在解决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和情感需求上,是无力的。
云梦泽人:确实如此。现代化可以为社会提供科技与物质的力量,但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而“巫”文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我们“无数代祖传下来的精神灵魂”。
詹乃德:这正是我希望表达的内容。现代性与传统并非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耦合、互相弥补”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科技”的方法来否定一切。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任何一种我们认为的“野蛮”甚至“落后”的民族,他们本身都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思维体系。这种体系正是当地原生态的心灵秩序,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精神与心灵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往往回到偏远而又淳朴的乡野,才能找到心灵的安宁。真正的解决之道,不是以破坏当地的原先生活方式为代价,而是要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重新理解和尊重那些与这片土地相契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原生态”的传统。
5.被放逐的灵魂:巫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与作用

云梦泽人:詹博士的见解,让我再次回到作品本身,特别是结尾部分。在作品中,我试图用“夸张变形之手法”来展现命运的“无处不在的强大与横蛮”。敏、焰、姑妈红等角色的命运看似不相干,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死死咬合在一起”。这种力量,正是深植于民族骨髓中的“巫”文化所构架的命运图谱。
詹乃德:云兄,您提到的“巫”文化,其本质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人类的思维基因”和“群体无意识”的体现。它代表了人与先祖、人与自然世界的“原生性”沟通方式。正是这种基于土地、血缘和历史记忆的深层精神结构,让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韧性。它使得我们能够“与原先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并找到“心灵的安宁”。在您的作品中,最让我动容的,便是敏的女儿“序”两次救父的情节。特别是结尾,她通过太外婆和巫阳的“法术”,驾驭着“四十岁的指甲”,用屈原《招魂》的吟唱,完成了对父亲魂魄的追寻与救赎。
云梦泽人:您说得太好了。我正是想通过这个情节,表达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召唤。女儿“序”代表着未来和希望。她的救赎行为,将屈原《招魂》这一古老的楚地巫文化文本,与“四十岁的指甲”这一当代具象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这枚指甲,既是敏的生命印记,也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我希望传递的,正是民族精神的回归并非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现代性的躯壳中,重新激活那些看似微不足道、被忽视的传统基因。通过新一代人的努力,这些被放逐的灵魂和被遗忘的记忆被重新召回,指引着民族走出迷茫。
6.总结与提升:四十岁的指甲与不灭的魂

云梦泽人:今天的对谈,让我再次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它不仅仅是对一段个人或家族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中心与边缘”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深刻剖析。这种对抗与融合,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源泉。通过《四十岁的一对指甲》,我们看到了从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的差异,到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巫文化的差异,再到近代以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与传统区域文化的差异。这背后所体现的,都是“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博弈与交融。
詹乃德:云兄,我相信,作者在游历诸国之后,在感受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大作。像歌德创作出《威廉·迈斯特》,像福克纳创作出《喧哗与骚动》,像马尔克斯创作出《百年孤独》一样。他正是在用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漂泊的民族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招魂”。
詹乃德:是的。这枚“四十岁的指甲”是血肉生命中不断新生、却又与身体分离的部分。它象征着那些被遗忘、被剪除的文化基因,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承载着我们最本质的记忆。
云梦泽人:只要我们愿意去驾驭它,它就能带领我们找回丢失的城池,实现灵魂的救赎。
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 维也纳石头巷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