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疑 ——应和冯知明武侠文学九问 温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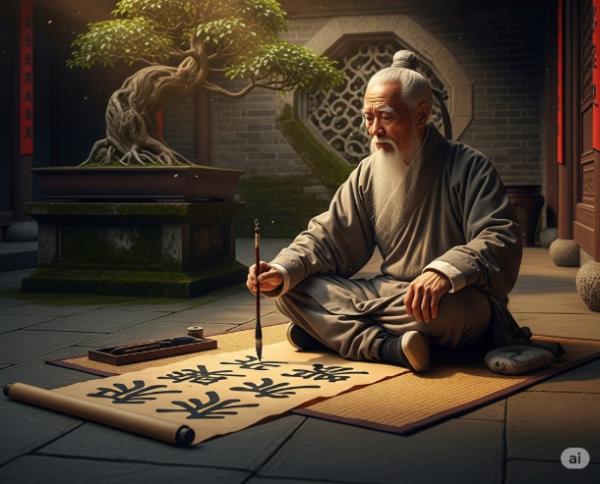
率直地说,对冯知明先生提出的“九问:武侠文学能否代表民族文学”,笔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不过,笔者同样就问题作出肯定答案后再衍生出疑问。这疑虑也正是笔者对武侠文学忧心之处,一旦问题能得到解决,那正是笔者所期待的,若不能,武侠小说在文学上的正面意义也难免遇上反向动力,这几个疑难正是因“九问”所逼出、催生的是谓“九疑”。
问一:“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笔者认为是的。笔者早年因地利之便,得以涉猎阅读相当多的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荷兰、日本、韩国,乃至葡萄牙、西班牙,当然是有英美的骑士、剑手、格斗、士卫、盗匪、武士小说,其中对侠本质上广义的追求和坚持容或比较接近,但对“义”的解说,以及著作在质量上都不及中国武侠文化传统丰富、繁复。我们早已习惯并视为寻常的,诸如“门派”、“秘籍”、“点穴”、“御剑”以及“义气”上的解释,都大为有别于其他国度的“骑士”、“武士”、“剑士”小说,对他们而言,接近难明或不可解,甚至是荒诞的。不过,笔者的疑问是:这些不易(但非不能,我们的武侠电影风行全球,在影像上已替我们解决了部份实际上的隔阂和拒抗)让人理解但又构成我们武侠文学特色的关键词,是否也正是造成让我们难以融入世界文学范畴之内的关卡?
问二:“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答案:是。武侠,不论今古,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电视剧、电玩,都已广泛流传,大众认可。通俗其实是一种美德,因为通俗也可以写得不俗,孤芳不一定要自赏;雅俗共赏,曲高和众,应该是值得努力的目标。不过,由于过去或现在的武侠文学创作人,不一定具备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万一这倾向越来越俗、越来越无聊,甚至内容越来越无耻,这就不是通俗的美德,而是俗不可耐了,这才是值得疑惧的。
问三:“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答案是相当肯定的。笔者就是一位海外毕裔,深切了解海外华人在阅读、观看、交谈、讨论有关武侠作品内容、人物、情节和理念时,同样也正在关心和认证了自己民族精神的特殊性。笔者也知道,在上世纪中期有许多旅居英美的华人学者、寄居海外的广大民众,都视武侠小说为民族精神的一个慰藉和皈依。不过,同样在高度凝聚民族精神能量中,也一样蕴含了极强烈对其他文化的排斥,有大一统以中华民族为重心的独尊作用,这属性一旦向偏执滋长发展,那就会造成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问四:“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是的。武侠文学是中国旧体文类(Genre)唯一能生存到迄今,而且还能开枝散叶、发扬光大的小说。它所依存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吸收传统和现代、中外的文化和文学上的特色、技巧、形式、内容,使得它的生命不断得到更新、新生。光是1970年代以来的武侠,文体和叙述、内容和题材,跟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白羽、郑证因,乃至梁羽生、金庸时的笔调、风格,已有极大的改变和转换,这才是使武侠文学源源不绝虎虎生风存活下去的元气。不过,变是变,开放是开放了,可是,文笔有没有在进步,本质是否更厚实,有没有更进一步逼近人生的真相?是否更成功地描叙了人性的善恶?还是仅在情节上越来越荒诞、描写上越来越粗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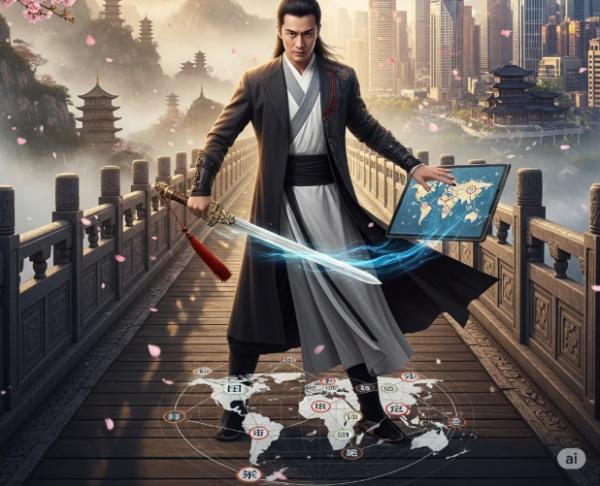
问五:“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就逻辑上和素材上的优势,武侠小说的确最有机会承传民族文化传统,只不过,问题还是在作者和作品本身,如果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修养和知识,而未能将传统文化适当糅合贯通现代精神,从殊相中表现了共相,建筑架构好稳健、才情的桥梁迈向世界文学的领域,我们也很容变成申辩和误读民族文化的真义,造成了偏仄的固步自封。
问六:“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这答案是绝对而明显的。不管中国功夫、武侠电影、还是特技打斗,武侠小说都是始作俑者,既曾天风海雨,也曾风雨飘摇,从学者到市井,从达官到平民,从小孩到长者,不仅辐射度广泛,同时渗透性无孔不入,同样颠复性和象征性也致广大而道深微。不过,这种影响有正也有反,辐射度愈大、渗透性最高,同样也会造成他人依据它所造成的危机和误读,来指证中华文化的畸形、暴力、嗜血、失去节约的那一面偏差形象。
问七:“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具体说:可以。但仍是要看作品。不过,问题是,武侠小说作品量如浩瀚大海,但写得极好,或能代表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作品,如大海之鲸、海里明珠,不一定捕捉得到、捞得着。我们需要的还是好作品,而不是自满自大。
问八:“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只有这点,无需置疑。能够生存一定有价值,已经能够长期生存的代表它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不过,也得正视一种正在发生的现象:武侠小说文字出版市场正在萎缩,武侠作品结集及杂志刊物,一度蓬勃后已正萎缩,除少数几位创作态度认真的青壮作家尚可独当一面,以及像《今古传奇·武侠版》等维持大局之外,一般销量都江河日下。以前是写的人不多,写得好的人更少,但看的人却很多;现正是写的人多,写得好的人更不少,可惜,看的人却不见得太多,真正轰动的和普遍为人所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武侠小说这种文类,若要长寿,得要注重培植和推广、引介和鼓励。不然就不一定能大能久,前景堪虞。另外,如果传统文类与题材只剩下了武侠文学为最具“自然愈合,长生不老”的能量,那只怕不能算是一个福祉。
问九:“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否正面引导新生代?”
这答案也是正面的。不过,一要看如何运用:教条式、规范式的约制和价值取向不适合运用在武侠文学作品里。二是要看作者的企图和文念,文学作品里的引导只能是潜移默化、移情作用里渗透进行,而不是指导式和单向权威性的。
九个问题都问得好,因为问题本身已提供了相当深厚恢宏的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有使命的张力,故此,也同时衍生了相应的疑问。一问一答,天问有疑,天意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