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是否代表民族文学》大讨论(二)

时间:2006年11月——12月
地点:天涯、新浪、搜狐……
事件:一篇名为《武侠文学是否是民族文学》的帖子悄然登陆中国人气最盛的社区天涯。不到一小时,点击过千,回帖上百。第二天讨论升温,网友展开热烈讨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不少。消息灵通之士打听到内幕,发帖者竟然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武侠文学刊物主编。如此一来,更多了不少攻讦者。第三天,帖子被热推到天涯头条。西南大学韩云波教授、社科院施爱东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刘忠教授、著名作家吴越等各抒己见……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报道,一场波澜壮阔的武侠讨论席卷百万网民,其声势丝毫不亚于上世纪末王朔VS金庸的PK。
一场关心中华衣冠、民族文化的讨论?一场贴大字报、抢学术山头的恶意炒作?参与者莫衷一是,旁观者各执一词。发帖者今古传奇武侠杂志社社长冯知明近日在博客上贴出一篇反思五四的文章,也许能帮我们透过云山雾罩,看到事情缘起……
赞同、反击——
冯知明:(吴越的反驳帖一出,楼主也反应迅速,贴出了这篇硝烟味浓重的帖子——)
九驳吴越先生
一驳“武侠文学不是中国特产”。首先,我在这一问里,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作为“文学形式”的武侠文学,而吴先生已经明确地对我表示了支持,他也认为“不能复制的是文学形式。”在吴先生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驳斥的必要了,但是对于吴先生提出的外国侠客,如佐罗和罗宾汉,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在国外的民间传说,或者是小说里,佐罗和罗宾汉之流的人物,大都是以盗贼的形象出现的,这客观地反映了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心理背景下,不太能接受游侠式的人物,所以要让他们做盗贼。在美化这些盗贼形象时,更多地采用了西方惯用的史诗英雄手法,他们的“侠意识”,带有强烈的随机性。我们的武侠文学,提倡的是“侠义”,义之所在,为国为民,这在西方是反映不出来的。
二驳“通俗的、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我注意到,吴先生使用了一个词“最广泛的”。如果仅仅说大众,也就罢了,能为普通大众接受的作品,确实不一定是好作品。但是“最广泛的”这个词,很是暴露了吴先生的精英情结,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性格中常见的狭隘面。如果连“最广泛的”大众都喜闻乐见的东西,还算不上好的,那这个世界检验事物的标准是不是永远都掌握在了“最广泛”大众之外的那些人手上?
我们并没有说武侠文学已经完全做到了这一步,但是武侠文学显然是在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我想,什么文学放到人民手里检验,都是最可行,也是最可靠的。
三驳“这个问题问得糊涂。”我问得并不糊涂,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民族文学的文学样式,如果连凝聚民族精神都办不到,那还算什么民族文学?至于吴先生的驳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混淆了概念:在吴先生这里,只要是人,都可以代表民族,吴先生把民族当成了一个人而不是更接近“抽象”的群体来考虑,所以吴先生才会说,“汉奸文学”也可以凝聚民族精神。此时,吴先生已经把自动脱离了民族的那帮人也当成了民族。
我劝吴先生仔细考量一下民族的概念。
四驳“什么文学形式不具有开放性?”吴先生其实已经承认了我这一问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一个文学形式如果具有开放性,将成为它是否能代表民族文学的一个标准。吴先生问得有些意气,好像我说了别的文学形式不可以代表民族文学,我们谈武侠文学,也只是把武侠文学放到民族文学这个大家庭里来说,我们包容,而不排斥。
五驳几乎无法开展,因为吴先生完全是在为武侠文学辩护,“武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他首先必须继承民族形式,然后才是吸收外来养料。中国武侠小说如果不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全盘西化,它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而是类似于翻译小说的四不像了。”
所以五驳,我只能感谢吴先生,并对吴先生并不能一以贯之对我的质疑表示遗憾。
六驳“外国人看了中国的武侠小说、武打大片,并不等于接受了武侠文化。”我在这一问里,对中华文化的辐射作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辐射性上。因为武侠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主要谈了儒家文化圈里,武侠文化的辐射性。在这个大文化圈里,众所周知,并不包括吴先生所暗指的西方基督文化社会。
立足于儒家文化圈,武侠文化的辐射性与儒家文化是二而为一的,在不具备充分的汉语语境的东南亚,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都是从阅读武侠小说开始。至于吴先生说的外国人看了武侠小说也不会有侠义精神云云,我想这谁也没有调查过,我们不能加以论断,吴先生也当慎之。
七驳“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按照吴先生的说法,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就不是国民性,此言智者当明鉴之。阿Q如何不能代表国民性?难道因为阿Q对国民的精神胜利的习惯讽刺得太辛辣?韦小宝如何不能代表国民性?难道因为韦小宝深刻地反映了国民的一种青皮心理?我同意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国民性,但是有些国民性是一以贯之的。阿Q和韦小宝式的人物,如今就不常见吗?
吴先生在此回避的是,武侠文学能否反映国民性。这个问题,留待大家继续讨论,因为我们也在思考。
八驳“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法想象能够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无视国法、纪律,到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吴先生先是有了个误解,就是在前文,把武侠精神简单地等同于了“侠意识”,在这里,吴先生把这一误解进一步深化了,认为大侠就“无视国法、纪律。”大侠首先都是尊重国家意志的,更尊重国民意志,这无视国法和纪律之说,只是由武侠小说中显而易见的夸张手法得来的。
武侠小说为了其可读性,不得不进行一些再创造,它之所以是成人的童话,就是因为这些浪漫想象,但是那种真正的侠义精神,是没有经过夸张修饰的,而是千百年沉淀而来。我们探讨武侠小说的生命力,是从一种文学的延续性上讲,吴先生把武侠小说能否有生命力,跟它能否书写当代社会联系起来,并提到“一些港台描写当代社会的武侠小说”,这有以偏概全之嫌。唐诗没有描写宋代社会,到宋代就不流行了吗?
九驳“大侠的中心思想是侠意识,是除暴安良。”吴先生对武侠精神的误解,是贯穿全文的。就是吴先生自己不断提到的“侠意识”,吴先生也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暴力行为。我们说武侠文学的教育功用,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感化新一代,先人后己、讲究诚信、舍己为人、重义轻利、古道热肠,这些都是侠义精神的一部分,也都不需要暴力。

朱近墨(武侠作家)
武侠是文学,只不过很多人不拿他当文学写跟看罢了。
重提那句老话,黄易的出现是武侠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他被媒体与读者吹捧起来足以证明当今武侠精神的堕落。真正的武侠精神散落民间四野,一旦故步自封、围建堡垒,跟正统、权威等等字眼挂钩,再不敢仗义执言、只会跟风、无千万人吾往矣之独立精神,武侠就难免失去了他的味道。现代武侠文学由港台发起,继在港台消亡,被起步较晚的大陆承继接过,但终究难免走上港台的老路。现在的武侠难有与金古温梁比肩者,关键他们没有震撼人灵魂的力量,多与其经历、素质、视野、人格难与前辈相提并论少了底蕴相关,加上各种新文化冲击,将更加艰难。不创新必死,该是开拓新路的时候了。
王晴川(武侠作家)
武侠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更贴切一点的说法应该是,武侠文学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学。
我曾经说过武侠文学的两点元气所在,一是武侠小说可以自然而然地乃至全面地引入传统文化,二是对侠义精神的弘扬。
从承载传统文化上看,自金庸梁羽生先生开始,注重将多元的传统文化引入武侠小说,这样不仅能有利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感,更能升华小说的意境,丰富作品的内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增强民族凝聚力,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乃至构建和谐社会,都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的吸收和继承。我以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上,目前没有一种文体比得上武侠小说。
正如冯知明先生所说,“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的功绩所在。”这一点,武侠创作的后来者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从侠义精神上看,武侠文学中描绘的那种至情至性和侠肝义胆正是这个日渐冷漠的现实中所缺少的。
吴越先生谈到,“今天的武侠小说,主要背景依旧是古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法想象能够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无视国法、纪律,到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样的形象,绝不是今天的法律所能容许的。”其实,优秀武侠小说要表现的主要是人性,决不是寄希望于现实社会中会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来包办一切。而且,认为读者读了武侠小说就会跃过法律去“到处行侠仗义”,似乎也太小看当今的读者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不会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武侠文学阐扬的侠,也不仅仅是“无视国法、纪律”,更多的是曾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大义和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平时期缺少英雄,但是社会还是需要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
所以,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承载,对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精神的弘扬,这两点正是武侠小说生生不息的元气所在,也是其最具有民族性的特色所在。
爆音爆食(武侠作家)
共同的想象构成一个民族
今天大家这个会主要谈的是武侠作为民族文学,能否代表民族文化,我根据这个说一下。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共同的想象构成一个民族,现在虽然西化的东西或者是在世界经济影响力比较强的欧美或者日本的大国,欧美所有文学实际上基础建立在圣经上,有人说,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始终是读不了西方文学的。虽然日本现在的东西,比如说电影、歌舞都很强,但是实际上在日本国内真正被捧到经典的还是时代剧,就是每年年末时代剧选择的时候,如果哪个明星被担当时代剧,他才被承认在日本国民中取得一个承认。
我觉得,侠义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就我们国内来说,真正著名的是四大名著,像凤歌说的,自主精神,实际上从汉末三国时期开始,中国对神的认识一直偶像衰败,中国始终没有神,反而真正被所有中国人尊敬的是一个人是关公,而关公最大的特点不外乎“侠义”两个字,侠义二字是真正在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多年下来,比如说各国的唐人街或者说56个民族走在外面的人,他未必把佛教或者道教的东西带进去,一般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关公像,就是侠义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武侠是很能代表中国民族性的东西。武侠分开来说是两个字,前面是武,后面是侠,侠的最观点的精神实际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去对抗一种东西,像现在的武侠大一点来分三个流派,金庸和梁羽生古体的武侠,侠之大者是他的关键,他里面实际上是对抗强权,这是最关键的。另外一个流派是仙剑派,他们到现在是奇幻,这个也是对抗,就是作为一个侠者他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仇恨或者是发展都是命运的东西,像今天这个会上还有人说新武侠要放弃侠之大者,说一些道家的侠,又说一些自我,实际上还是东西对抗自我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武侠还是蛮符合国人的精神。
同样我认为武侠是很开放的东西。对于现在奇幻和动漫、游戏这三样在市场上挤压了阅读,但是这个还是从两个方面来说,奇幻的基础是西方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东西了,它跟武侠是两种精神风格,奇幻的基础是团队,就是魔法师、骑士、不同的团队组合一般都是三到四个人,是以团队形式表达一种精神,去冒险;武侠最终落实到英雄、武侠最终就是在追求英雄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一把刀,比如《射雕英雄传》宋朝末郭靖怎么怎么样,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实际上现在整个发展,在西方奇幻这一块,世界观也改变了,比如说现在比较红的是《魔戒》和《哈利·波特》,这两个对照,魔戒是传统的奇幻,他还是团队化的,实际上小矮人武也不行,魔也不行,但是他后面的团队共鸣的,而《哈利·波特》是反过来,是《哈利·波特》一个人最大的主角,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们用的是魔法,反而跟中国传统的武侠,一个人一把剑的精神是糅合的。
动漫和游戏它不是一种风格的内容,它是载体的东西。现在动漫和游戏加上动画、漫画他们是一种载体的问题。我前段在北广这边听课,实际上电影改编的要求,最基础的是文学性,在文学性之上才是戏剧性。实际上动漫如果要选剧本的话,他只不过在文学上多一点要求,可能柔和性高一点,游戏对于脚本的选择,尤其武侠脚本的选择,要求他有针对性,比如成长性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武侠作为诉求的东西,他跟奇幻有柔和、有对抗,但是它对于动漫和电影来说,它反而是动漫和电影的基础,就是说武侠你能够发展得很大,很广泛,反而能让许多动漫、游戏和电影让武侠来选择剧本。比如说打压的情况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现在来说是需要一个开放想象力的阶段,比如说像步非烟说的随便什么进来都可以,现在武侠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开放想象力去写,也能够超越金庸,现在商业是销量的问题,你销量只要过三万到五万足够可以养活一个作家,因为周边产品的开发能产生其他的需求。
说到最后,武侠这个最基础的关键,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武侠我才来写的。
最后我觉得作者要有写武侠的耐心。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当初是四百多人,港台是四百多人写武侠,出名的不多,现在写武侠得更多,网上在写的可能更多,三四年前的时候,武侠到底能不能市场化,大家心里没有底,但是还有人在写,就是有人在喜欢这个东西。如果今天大家觉得不行,武侠被奇幻打压了,武侠被YY打压了,写这种东西不如写YY,这种精神跟侠的道理本身违背了,侠义最终的目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嘛,就是说只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就坚持续写,经过一段时间,就像李亮,他就是坚持写实验的,步非烟成功了三年,他和步非烟陪跑了三年,但他的东西还是有人喜欢,可能是没有一百万,但是有五万就可以了。
就算是红学现在很盛行,但是80年代“红楼梦”电视剧播之前,红学也是默默无闻的,所有的东西需要一个机会,大家就是有一个耐心,你要有写畅销书的耐心,你凭自己的感觉去写,你凭自己的爱好去写,总是有人跟你合拍或者是慢慢的时间去冲刷,你的作品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了。

施爱东(社科院研究员)
我一位朋友仲林在他的论文中说道:“仔细追溯起来,民间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民族意识促使人们去弘扬民间文化;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广泛认同又促进了民族认同。在民俗学诞生之初,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德国、在芬兰、在英国莫不如此。”
武侠小说虽然不是直接的民间文学,但武侠小说有着浓厚的民间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武侠小说简单的思想负载,以及它在情节设置和语言运用方面的程式化倾向,使它具有了最广泛的接受群体和最快捷的消费速度。
金庸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有,那也是副产品),反是与小说中大量引入的模式化的民间性成果有关,比如,具有戏谑功能的周伯通、桃谷六仙等福将形象,作为巧媳妇的黄蓉与作为傻女婿的郭靖的形象,具有浓郁史诗英雄特质的萧峰形象等等。而偏于悲剧色彩的《连城诀》《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等,就远不如其他一些具有欢乐精神的作品受欢迎。
武侠小说的读者,显然不是精英思想的受教育者,他们是欢乐精神的消费者。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最起码的事实,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几乎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先天地决定了它的消费本质,而不是时代精英思想的承载者。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的叙事语法,它的广受欢迎、快速消费等文类特征,正是基于读者对这一叙事语法的熟悉,这是创作者与接受者历经千百年的双向互动而得到的一种稳定状态。作者在具体创作中的“自由创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限变异”,也即我们常说的“带着脚镣跳舞”。“所谓具有开拓意义的优秀作品,很可能不过是99%的‘旧’,加上1%的‘新’;可正是这1%的‘新’改变了作品的质,实现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而这所谓99%的“旧”,恰恰是艺术审美的民间性长期作用于武侠小说创作的结果。
龙辰——
第一问: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是。这个问题与武侠文学是不是民族文学殊途同归。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不错,但真正民族的东西却又无法真正成为世界的。比如说民族文学中代表的唐诗宋词,这些无论如何翻译,只能为外国人所了解,而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血液中、骨子里的东西。如同看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固然承认它是名画,但怎么能比得上兰亭序;再如看了荷兰的拦海大坝,固然惊叹其壮观,但在心中如何能比得上长城。因为民族的东西所引起的不仅是赞叹,而是一种体认。这个思想我在“秋寒山河”结尾处也有所描述。问武侠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是否具有不可复制性,就如同问京剧在世界戏剧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样。武侠文学的背后不只是文学问题,如同京剧背后不只是戏剧问题。为什么武侠小说只在海外华人圈中流传呢?这充分说明,只有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积淀背景的人,才能接受武侠小说。金庸小说虽然被翻成了英文,但我相信没有几个洋人能读懂其中三昧。简单地说,笑傲江湖背后是三千年中国政治斗争,这洋人读得出来么?既然读不出来,武侠文学自然具有不可复制性。
第二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真正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具有高度的通俗性,否则也不会成为经典。许多我们现在看来阳春白雪的东西,在当初都是流行元素。还举唐诗宋词这个例子,那是在当时社会中广为传唱的东西,只怕有些像现在的流行歌曲。真正流传到现在的是当时流行歌曲中最经典的罢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相信不是每个井水处都有诗人吧。其他如四大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小说的来源本来就是话本,如果没有高度的通俗性,如何能流传至今?通俗并不等于庸俗。谁敢说鲁迅的东西不够通俗?那些半文半白、今日看来语法似不通的文章在当时不是最流行的通俗作品么?
第三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这个命题有点拔高了,但不可否认武侠文学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正如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所昭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复兴有赖于民族精神的觉醒,而不仅仅是经济数字的不断攀升。自从近代以来,中国苦难深重,以至于民族精神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挫折与损伤。坦率地说,我们现在的民族精神中,已经没有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气象,也没有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盛唐风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百年欺凌与苦难后重拾信心所必经的阶段。这样一种现象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我们对外宾的优待程度要超过本国公民,而在其他国家,国民待遇都是优待的同义词。武侠文学,无论是传统武侠,或是新武侠,甚至大陆新武侠,其在精神领域都是一脉相承,即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自由,等等。民族精神会影响到每个国民,而每个国民精神的提升,也必然推动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形成。只有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具有大国风范与气度,中华民族的精神才能再度弘扬。现在的新武侠文学,已经有了很多新元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人性的歌颂与追求。在这一点上,武侠文学有益于民族精神的确立与凝聚。但是,我也不赞成将其无限拔高。因为武侠文学毕竟只是文艺形式的一种,我不赞成为上纲上线而要求所有文艺形式都要有教育意义。
第四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事实了。事实上,除了武侠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或艺术形式,极少能在其发展过程不从其他文化吸纳有益成分。新武侠文学,已经加入了诸多其他文化的元素。单从技术角度来讲,侦探手法、意识流、蒙太奇等的引入,不都是如此么?事实上,创作武侠的人生活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上,根本不能避免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知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从其他文化中吸纳有益成分。封闭而非开放的武侠文学,是不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第五问:武侠文学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这个问题如第三问。不要拔高武侠文学的作用,只能说武侠文学中含有很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谁能说自己没有或多或少从武侠文学中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但要谈到继承,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武侠文学来继承,这与其说是武侠的幸事,勿宁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武侠只是承载中华民族文化的多种形式之一,其功能不应被无限放大,对其的期许也不应太高。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是武侠的责任。毕竟武侠只是一种文学形式。
第六问:武侠文学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若说武侠文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则要先肯定中华文化极具辐射性。那么这一辐射性的标的是什么。是海外?是他国?还是中国人?抑或海外华人?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感兴趣不代表真正认同或接纳。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京剧,如太极,如中医,等等皆如是。同样的,我坚持认为,武侠文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或者说,是写给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人看的,如海外华人。很难说,一种文学形式能有多大的辐射性。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纠缠百年的命题。自从近代以来,关于这个命题的讨论与争论常常引发对中华民族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林语堂之吾国与吾民,柏杨之丑陋的中国人等等。而这些又都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产物与直接结果。到底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什么?我无法说清。三千年前的中华民族、一千年前的中华民族、三百年前的中华民族与如今的中华民族是否具有一致的国民性?我看未必是。因此,恕我冒昧,武侠文学是否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一个伪命题。是否可以这么说,武侠文学是根植于中华土壤的文学形式,反映与体现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第八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是肯定的。侠义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这一点恐怕毋庸置疑。追寻正义、善良、美好的事物,不但是武侠文学,也是其他一切文艺形式的永远主题。只是侠义以武的形式来表现,更能为人接受罢了。两千年来一直如此。当然,有人质疑刺客列传、水浒传等到底是不是武侠文学,我们无须对此进行争论。无论它们是不是武侠文学,武侠精神应该贯穿古今。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如此。社会之和谐、公平与正义,甚至是每个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看电视,经常可以看到,警察抓住嫌疑人时要大声背诵“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法庭上对你不利的证据……这是什么?这便是正义的精神以程序正义的形式体现。程序正义的目的是维护实体正义,而实际上,实体正义是永远无法百分百保证的。因此,对正义的追求自然应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种追求可以表现为人性、自由、爱情、理想、热血……这些又无一是武侠文学拥有的元素。
第九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这个问题与第三问有相似之处。在第三问中,我表示,我不赞成为上纲上线而要求所有文艺形式都要有教育意义。我同样认为,武侠文学不能搞得像政治思想教材。毕竟,武侠文学也好,或者直接用武侠小说这个词,还是以故事性与娱乐性取胜的。试问,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如果不是包含在其丰富的小说情节中,有谁能看得进去?武侠,在这个意义上像郭德纲口中的相声,第一步必须先让观众笑出来,第二步再谈教育意义。一个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艺术形式,根本谈不上有教育意义。只有先喜爱了相声这种形式,再从其构成元素中如太平歌词,去体会做人的道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中国现代教育的悲哀,就是功利性太强,太强调立竿见影。须知孔夫子两千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每个人情况不同,教育最大的功能应该是在知识上传授,在做人上引导,而非在知识与做人上灌输。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武侠文学对新生代、或者说对特定对象有何显著的教育作用。武侠文学只要做到不要诲淫诲盗,能从中看出些积极的因素就好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能选择今天这份职业,也许还是受了一点点武侠理想主义的影响。在十年前那个少年的心中,郭靖守襄阳、萧峰息兵戈,都是能引起自己羡慕的事情。
陈天下——
冯兄的《九问》问得好,武侠文学被泼的污水太多,如何满足袁良骏王朔之流,也被人误解太多,不仅一般民众误解,甚至应该知书明理的读书人有误解,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误解,自命为知识分子信奉民主与科学、法制与理性精神的人,也在误解武侠文学,不仅是学术界,出版界,甚至文学界,甚至文学界里最不应该误解武侠文学的文学评论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在误解武侠文学,因此,冯文九问,在问武侠文学一方面被社会与民众认可接受到常识的地步,一方面,又被贬得与色情小说、暴力迷信等精神污染同一程度,就像元代把读书人贬得比娼妓还低下,叫“八娼九儒十丐”。搞写作的人在一起,若有人声明自己是写武侠的,众人便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仿佛他是小偷似的。搞评论的,若叫他评武侠,他会觉得是污蔑他的智慧的学识似的,连忙落荒而逃。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不承认武侠文学的地位的,评奖什么时候奖过武侠小说呢?文学年鉴里,什么时候写过武侠文学呢?《傲慢与偏见》这篇小说名,正好是评论界文学界某些人的心态的最好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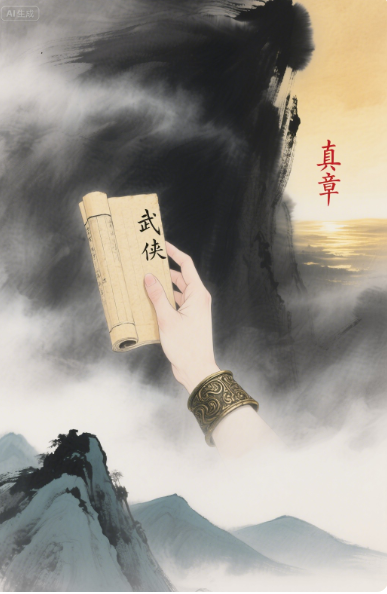
罩在武侠文学上的学理的迷雾,应该拨开,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还武侠文学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厘清武侠文学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这对繁荣创作,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精神,甚至对振兴中华民族,都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看似小题,其实可以大作。谁说是小题?这是大题目。能作好这篇文章,至少可以当博士。这篇大文章,可作为文化立国的对策之一,应予重视。中可作为振兴武侠文化武侠文学,为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文学的百花性,增加一大证明,为武侠小说创作指明方向,有利于武侠文学健康成长。下可纠谬误驳偏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求真求实,回到常识,让人理性看待武侠,这对武侠文学的作者,编者,读者,以及一般社会民众,都是有好处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么,洞明武侠文学真相,至少是一样学问,明白武侠世界里的人情世理,也是一篇不小的文章。若有人小看这个问题,以为是不辩自明的伪问题,那就不是出于对武侠文学的无知,便是出于对一般民众的认知水平的无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