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的感恩与敬畏 ——读冯知明散文集《灵魂的家园》 刘忠

散文集《灵魂的家园》中,温情眷顾的叙述、抒情笔调下,湾台的乡风民韵徐徐吹拂,小镇的人情风物悉数登场,少年玩伴的稚拙嬉戏生气活现,祖母祖父、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平淡如水的故事缓缓流淌。记忆因流水而生动,文章因真切而感人。《打鼓泅》中因逃学“游泳”而遭遇惩罚的回忆,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圆到三味书屋》,“红色”教育的乏味从字里行间见出,少年玩伴的率真也在乡下“狗爬式”游泳——打鼓泅中隐现。《小镇·小厂·红衣少女》的小镇、小厂温馨可亲,那里是作者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作者朝霞般初恋孕育的地方,少女的矜持、醇厚不仅让作者度过了一段不被人理解的时光,而且一句平淡的祝愿,“你一定会有出息的!”至今仍激励作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近故土,走进乡民们的心灵世界。《童婚》中,童婚仪式的繁文缛节,以及“我”与姑妈侄女亲上加亲的童婚之旅的追忆,让我们随着冯知明柔情缱绻的笔触一道退回到往昔,品味那份伤痛多于柔情的凄美。
有人说散文贵真,大凡好的散文都不乏真感受、真性情、真思考,《红头绳》《捉鱼的童年情结》《五元钱的故事》《示众的老鼠》中,我们读到了这份蒸腾着血气的真性情、真思考。“红头绳”“五元钱”见证了贫穷年代的无奈与孤寂,同时也记载了童心的真纯与灼热。时序的更迭并没有抹去记忆的印痕,许多年以后,作者深有感触说,“我开始懂得贫穷是对美的破坏。”在《外婆湾前有条河》《梦中的绿豆鱼》《挥之不去的思念》《母爱无痕》等一组写亲人的散文中,作者怀着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敬意,让时光吹过岁月的河,任亲情摇曳为一个个往事。外婆对“巫术”的诚笃、祖父对孙辈的慈爱、父亲的通达、母亲的含辛茹苦已经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为文为人的精神理由,“给我力量,给我光亮,给我勇气”。流光已失,生活有痕,他们作为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个中甘苦是淘洗不去的思念,是萦怀于胸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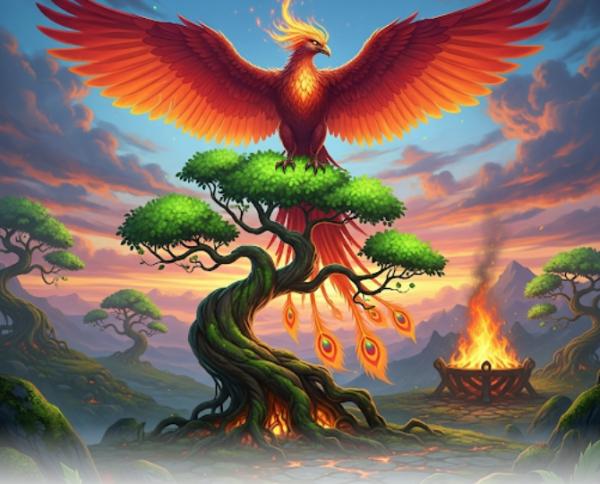
千百年来,村庄作为乡民自发居住的地方,或者临山,或者傍水,冯知明的老家湾台也是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寂寞地生,寂寞地死,祖辈如此,父辈如此,邻里乡亲亦是如此。《表哥》《幺舅》《逃离大学的诗人》《乡村匠人》中的表哥、幺舅、逃离大学的诗人、乡村匠人的箍桶佬、货郎、补碗匠,为了生计,他们四处奔波,一生一世的付出,而又一生一世的失落。“他们躺在自己做的小屋里,坐在自己种的大树下,劳作在自己的田地上”。湖上来的风常常变换方向,但是他们滞涩的精神世界却未曾有大的改变,多子多福、迷信守旧、安贫乐道等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关于此,《表哥》中,冯知明有一段颇为精到的议论,“在新旧观念的更替过程中,旧观念有时像一块旧伤疤,遇到阴雨天气,会在你的某个部位隐隐作痛。不信,在某个阴雨的日子,试着摸摸你的旧伤疤看看。”
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面对那些偶发的、神秘的现象,年少懵懂的“我”以及成为作家的“我”,一如当初时的惶惑迷茫。虽然随着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的增长,许多不解有了确定答案,但新的不解又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生活在一个为声电包围、科技主导的社会里,生活在无法把握自我的精神幻像里,难道我们能确信比那些生在乡村,又在乡村冬夜里默默死去的乡亲更有意义吗?作者再次感受到作为个体的人的有限,大自然面前人的委琐渺小,命运面前人的无能为力。于是,在《天眼》《血地传说》《成长的忌讳》《叫魂》《生命中的暗示》中,我们读出了作者对生活的敬畏之情。《天眼》中,作者用“据说,十岁以下的孩子都有‘天眼’”的转述方式,略显暧昧地道出“真情”:“童年的一天,我亲眼看见过它,它成为永存在我心灵之中的奇迹。”也许正是源于这种对生命、对生活的敬畏,作者才一再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我相信,在那片万物有灵的土地上,还有一种鸟在止息,它的名字叫凤凰。它还没有失去最后的耐心,即便是青碧的梧桐树已被伐尽,即便那熊熊的火堆已经燃起。”这种对生活的敬畏之情在使我们的心灵充溢祈盼、感念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视生活、怀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