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峪的宣传战
【本文引自笔者《长城抗战/日中档案比较研究,新版》罗文峪战斗一章】
罗文峪之战,战略面结果是二十九军胜利,但战斗中二十九军各部仍付出了惨重代价。据北平军分会统计,宋哲元部死伤如下:
暂编第二师亡469名,伤537名,死伤共1006名。
第三十八师二二八团亡70名,伤130名,死伤共298名。
第三十七师(二一九,二二〇团 )亡37名,伤105名,死伤142名。
合计亡576名,伤772名 。死伤数共1348名[1]
对比下,日军方面记录为 亡6名, 伤39名,死伤合计45名。死亡率比1/96 ,负伤率比 1/17。是整个长城各口战斗中,国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称大捷仅仅是战局方面的推移结果,从伤亡数字对比看,实为勉强。
第五节 日军失败原因及国军的大捷宣传
日军的罗文峪作战失败原因,考虑有如下几个要素。
1. 中国军在数量,武器面的优势。总兵员6000余名[1],4个团以上,约等于日军4倍。
2. 后方补给面的优势。罗文峪离遵化县(兵营及兵站补给地)仅9公里。有公路运输线,仅一小时既能将援兵派到前线。而日军离出发地承德有120公里,没有通车道路,山地道路火炮也必须驮载,为赶到罗文峪作战,早川支队在途中即花费了近4整天。当然,几乎无法补充粮秣,弹药(有运输机一架在佛爷来附近补充的记录,却迫降,机体大破)。此点,和有后方道路的古北口,喜峰口战场完全不同。发挥不出关东军机械化作战优势。
3. 地形面优的势。尤其是罗文峪,大毛山方面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所以日军只能选择山楂峪口两侧为主攻目标。地形不利,兵力,弹药绝对不足,是早川支队放弃战斗的理由。可认为也是关东军和第八师团的战略部署错误。接此教训后,第八师团主动放弃了对条件类似的马兰关的攻击。
4. 国军的士气。喜峰口战斗后,经军内部表彰,媒体外部报导,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名声大噪,被视为抗日英雄部队。精神上和物质面的声援,支持,捐助来自全国各地。罗文峪战斗正好发生在宣传期间的高潮。宋哲元也有意利用喜峰口方面的大捷宣传效果,来鼓舞罗文峪方面的战斗的士气。虽宣传内容不实,但效果确实对罗文峪官兵的士气发生了一定有利影响。
宋哲元的对外宣传
和喜峰口大刀队夜袭战同样,罗文峪战斗的歼敌报告,也同样是一场出色的宣传战。特别是此战斗中,第二十九军第一次取得了战略面胜利的结果。
有关二十九军的战斗报告(包括喜峰口战役),可称存在两个颜面。一个是军内,作战记录的内部资料,另一个是对外宣传的内容。前者目的是为了掌握战局实况,运筹兵力,武器配置,或提取经验教训为将来参考,所以有务实严谨之必要。而后者目的仅仅是为了鼓舞军民全体的抗战士气,所以不管事实如何,胜利报导中歼敌战果越多越好,所以两者间出现巨大差距。下面比较一下有关罗文峪战斗的两种数据。
先看一下军内记录。有关日军部队的人员,武器装备,北平军分会《长城各口战斗》中称:
据兴隆县坐探报称,双庙之敌系日本第三十一联队早川部,约步兵十二连,骑兵二连,炮兵一连,炮四门。平射炮一连,机关枪二十余挺云云。[2]
17日午前0630“据侦探报告,快活林,前丈子一带已发现敌步骑炮联合之部队约两千余人有向我罗文峪山楂峪前进之样”(同36页)。
“敌与我此方面作战之部队为早川大佐所指挥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为基干并附山炮二十余门飞机一队(约战斗机及侦察机十二架)”。(同39页)
即早川支队是步骑炮联合的一个联队,约2000名。此数和实际(约1600名)并无大差。武器方面掌握的也较准确。下面再看一下宋哲元对南京军委会的战地报告,虽最初情报不明时有夸张,但随着情报的增多,准确性提高,错误数字被修正。
3月19日,宋哲元曾报告 “据俘虏供称该敌系卅一联队及第八联队之一部加以蒙韩伪军共计八九千人并附汽车五十辆装甲车三辆飞机五架…”[3]
3月24日, 宋哲元在南京呈报罗文峪连日战斗经过情形时,再称“敌以早川大佐率第八师团之卅一联队及炮兵第八联队之一部约千余人附汽车飞机”。
两则都是对南京军委会的内部报告。前者是引用俘虏口供,敌情被夸大是有情可原的,反正未出自家之口。后者(5天后)是敌情侦察报告,可见已经掌握到较准确程度。来犯罗文峪敌部队人数被修正为“千余人”。且其中也不像对外的宣传内容那样,只字未提歼敌战果数字。仅称 “敌因伤亡不支,于皓辰向半壁山溃退,获得日本旗子伪国地图支队命令等物甚多”[4]。
再看一下军内部的基础史料,北平军分会1933年制作的《长城各口之战斗》。有关战果,统计表中除了第二二八团记录俘虏敌官佐1,士兵22名的数字外,并没有记录歼敌数据存在。只在战斗过程叙述中散见 “死敌一二百人”,“此役毙敌三百余人”(36,37页)等零星的,不确实描绘,应来自下级部队的战场报告,属于非正式数据。不统计敌伤亡数的理由也很简单,即无证据。由于日军自主撤退,第二十九军未能打扫战场,所以也不可能有敌军的死伤统计。
以上是内部的战史档案内容。可称都比较严谨。下面再看一下对外宣传内容。同为宋哲元本人还有另一个对外的颜面。
罗文峪战斗刚刚结束,3月20日,宋哲元回到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事处,午后2时,在各界众多的记者面前,发表了《宋总指挥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讲演)。当然要提起刚刚全面获胜的罗文峪大捷,宋云:
(喜峰口)敌人进攻即不得逞。十六日晨。以五千人之众。偷击罗文峪。其中正式日军约有两千。其他为朝鲜蒙古热河各杂色部队。第一日晚攻击未能成功。第二日自清晨六时起。至晚六时止。敌人完全用重炮轰击。占领一高山头。夜间我方派兵一营。抄袭敌人后方。敌不支退去。我军遂又将山头夺回。 白天敌人又想来夺。我军奋勇死守。双方刺刀肉搏数十次之多。我方又加上刘汝明师生力军一部作战。至十九日为止。敌人伤亡。又有二千名左右。已自动向后撤退十数里。[5]。
在此出现的罗文峪之战,开始时间变为错误的16日,敌军为五千人之众,结果歼敌二干余名。此对媒体公开的3日间激战,歼敌2000余名,后成为一个罗文峪大捷定说。战后又作为历史证据,被大陆的战史研究者纳入学界的战史记录中。
一面,宋哲元的讲演并不是在信口开河。内容有一定根据,来自何处?若核对当时的媒体报导,可知都来自第二十九军宣传口对媒体提供的前线战果速报内容。如以下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可见消息来源记载为“军息”。
(中央日报20日)中央社北平十九日电军息罗文峪之敌为日军三十一联队及第八联队之一部,系铃木旅团所属,加以蒙韩伪军共约9000余人,并附有汽车50余辆,装甲车3辆,山炮4门,平射炮6门,机枪20架,系由朝阳平原绕道而来之生力军,铣(16日)晨敌骑先头部队开始向我罗文峪阵地猛冲,激战多时,被我守兵击退,晚八时步炮联合复一齐猛烈进攻,我军迎头痛击,毙敌甚多,迄筱晨,敌更以主力向我山查峪口阵地同时猛攻,我军奋勇抗战,白刃相接,血战终日,阵地得失,往复十余次,是役我李曾志团长负伤,其余官兵伤亡亦众,巧(18日)夜十二时,我军以当面之敌顽强过甚,急派有力一部星夜绕击敌后,水泉峪附近之敌,因左侧背受我威胁,于晧(十九)清晨纷纷向后溃退。
下面是媒体按宋哲元讲演和军宣传口提供的战果报告编写的宣传册子《长城血战记》[6]中罗文峪战斗一节的内容。有关敌军数量:
(日军)抽调早川止第三十一联队。第八联队长濑。谷义一两部。附骑兵一连。装甲车三辆。山炮四门。平射炮六门。机关枪四十架。飞机二十余架。联合蒙鲜伪军两旅,共万余人…向罗文峪关外挺近。( 34页)
有关杀敌数,称:
16日“毙敌甚多。我军亦死伤七百余名”。 17日“战至下午二时,卒将敌之第一道防线击破,毙敌千余名,生擒敌指挥官三人。…三时许。续将敌二道防线击破。…敌吉田少佐。死于此役…我军本日。死伤约三四百人”。 18日敌“复调步骑炮协同部队约三千余人。…向我罗文峪山渣峪沙波冈猛冲。…(我军)待敌接近。挥刀猛砍。格杀无数。并活捉其骑兵大尉一人。…血战肉搏。历五小时之久。敌向我猛攻十三次皆被击退。是役毙敌约四五百名”。( 39页)
另有我军夜袭“砍杀敌人六百,虏重机关枪十一架”, “计敌因被砍伤亡者百数十名。重机关枪虏十一架。破坏五架。抬回六架”。内容,等等。(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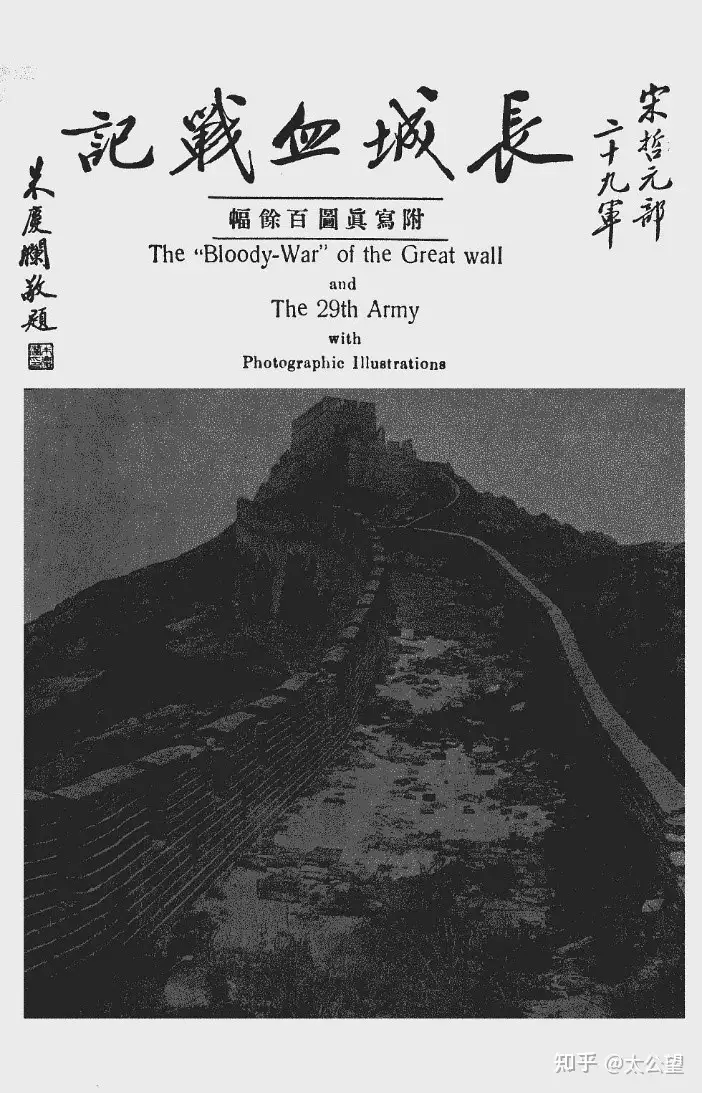
图表9-15 《长城血战记》第二版(照片版)此媒体公开的宣传册子,现在成为国内长城抗战研究学术的依据
其中 “砍杀敌人六百,虏重机关枪十一架” 等消息源,均来自“中央社北平十九日电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对外发表的“晨十时接前方电话报告”。
再看一个貌似战史档案的《华北军第三军团抗日战役阵中日记》内容,更为虚悬。首先记录了前述无中生有的16日歼敌数百名的激战,17日战斗又称昼间,突破敌两道防线,“毙敌千余名,生擒敌指挥官三人…敌吉田少佐死于此役,我刘营士兵伤亡奇重”。夜间(王合春)大刀队夜袭,迫使敌向北溃退。“是役王营长阵亡,士兵伤亡三四百名,敌较我伤亡在五倍以上”。“现在罗文峪口山渣峪一带与我作战之敌兵力约有五六千人之谱” [7]。18日战斗记载要约如下:
敌兵3000余,晨一时猛攻山楂峪口,刘师长亲率兵应战,杀敌无数,敌仓皇向后溃退。午刻,敌更大之部队再次攻击十余次,皆被击退,“是役毙敌四五百名,我伤亡亦百余人”。晚十一时,敌以全力再次猛攻,李金田旅由沙宝峪口向敌侧背绕攻,祁团长复自左翼向敌背后出击,刘师长见敌动摇,令各部全线出击,血战竟夜,将三岔口,快活林,古山子,水泉峪,马道沟一带完全占领。是役敌伤亡千余,并获机枪十一架…敌受重创,全线狼狈溃退[8]。
到此还未适可而止(战斗实际上18日结),甚至继续创造出莫须有的19-20日战斗:
侵犯罗文峪山碴峪口之敌,连日经我痛击加李祈(祁)两部昨夜绕攻,损失甚钜,士气大馁。至今晨〈19日〉二时敌拼命与我格斗肉搏,血战至午时被我砍杀数百,敌遂狼狈向半壁山佛爷来溃退。十时敌复调杂色一旅及三十二联队向我罗文峪口,山碴峪口,冷水头口,大安口,马兰关口进攻,激战终夜,卒未得逞,至拂晓(即20日)全线退去。我第一团乘此时机扫清战场得敌铜盔百余个,并在敌阵亡之岛村大佐身上搜得满洲地图,日记并敌军第三十一联队由承德向罗文峪出发之命令等。计此役敌伤亡大尉以上军官八员,内有吉田,早川两个太(大)佐,我军伤亡甚微[9]。
资料虽冠《阵中日记》名,从内容可知是日后编纂的对外宣传内容(战功记录)。和《长城血战记》,《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等类同,都出自军参谋长张维藩和其文人写作班(北平东方学社孟宪章)之手。据研究者X氏的对比罗文峪战斗记述内容的考证结果,先出者是孟宪章编《长城血战记》(3月26日初版)内容,实际上是对各媒体报导内容的剪切,以“军息”对外宣传内容为中心构成;以此为基础加入部分军内报告资料,战斗要报后按日期改写完善的内容是张维藩编《华北军第三军团抗日战役阵中日记》;在此《阵中日记》基础上张又进行进一步删改润色的是《陆军二十九军长城战役经过》。而《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内容,则是后年经宋哲元之女请求,对张维藩《陆军二十九军长城战役经过》的全文转录。貌似越改越真实有据,实际越改越乖离历史。由于与事实不符,且错误谎报连篇,所以记录长城抗战的国军档案《长城各口之战斗》,和之后的正统战史,并未采用此第二十九军系列资料中的内容。但在国内民间,伴随着不朽的大刀队抗日神话,此故事至今仍流传甚广。
如上所述,罗文峪战斗战斗进行中,或刚一结束,歼敌2000名的大捷说已被第二十九军的宣传喉舌对外公开。并通过宋哲元的记者招待会讲演,媒体报导,第二十九军的战斗记录等,流布于全国各地。而实际死亡比90对1的惨烈战果,在台海两岸至今无人所知。
第六节 历史的继承方法
以上,对比了军内,军外记录报导,指出来自内部的战斗记录和对外媒体宣传之大差。内部的战斗记录,根据电报,命令等编成,虽然也会有误但方法一般都比较严谨。而对外宣传中出现的内容全般都有大幅度人为的渲染,夸张。由于内容明显不实,对于后者,经过史料鉴别,批判的战史研究等一般都不予提及,采录。但一般普通民众,可接触,信赖的多是这类流布于媒体的“大捷”消息。问题在之后的战史研究和历史记录,到底继承的是哪一种?是内部记录,还是对外宣传?下面分析几种后出的战史记录。
上世纪60年代于台湾编纂的国军正统战史《抗日战史13/滦东及长城作战》,基本严格继承了1933年北平军分会编史料集《长城各口之战斗》内容,称罗文峪之敌为“步骑炮联合之敌约二千余人”。战斗17日开始。结果为敌突然发射烟幕弹数十枚后,向佛爷来,半边山自动退去。记录了自己方面的损失数(第二十九军在整个冀东作战中的死伤失踪总数为4631名[10]),但没有触及到任何歼敌数字。比较起来是迄今所有战史中最中肯,严谨的记录。
而国内(大陆)的战史中采录的却多为《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或《长城血战记》《第廿九军华北抗日战斗经过》等第二十九军推出的宣传内容。比如江绍贞《长城抗战》称:
3 月15 日,日军早川支队第31 联队附骑兵一连,山炮4门、平射炮6 门,机枪20 挺,经寿王坟、双庙、半壁山之线南进。16 日拂晓,日骑兵向我罗文峪正面进行攻击,企图先将该地最险要之三岔口占领。...随后日炮兵部队集中炮火轰击罗文峪城垣,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猛烈进扑。我军据城垣及碉楼为阵,双方展开拉锯战,...是日晚8 时,日军再以步炮联合部队发起进攻,同样被我军击退。”…“于17 日晨8 时起,集合步骑炮联合部队约三四千人,由半壁山分向罗文峪、山查峪、沙宝峪三处同时发起进攻,先由炮兵猛烈发炮,继由20 余架飞机低飞助战”。 “此役打死打伤敌官兵百余人,缴获重机枪11 挺。[11]
采用的是《长城血战记》中,宋哲元的16日开战说,和第二十九军驻平办事处”对外发表的内容(缴获十一架重机枪等)。 虽然敌军数,战果方面都有夸张,但比起国内其它几个专著,还算是一例有部分谨慎之处的记录。特别是“此役打死打伤敌官兵百余”(非歼敌2000名说),很可能是参考使用了日军的战史档案。
第二例,看余子道《长城风云录》[12]
16 日凌晨,敌先头部队骑兵,沿半壁山开始向罗文峪正面发动进攻。...战斗之烈,实不下于喜峰口,卒将敌击退。“17 日,日军步骑炮联合部队三四千人,由半壁山分向罗文峪、山查峪、沙宝峪进攻”,18 日,日军再次发动猛攻。刘汝明亲率第一团手枪队应战。…双方“血战5 小时,敌猛攻3 次,皆被击退。歼敌四五百名。我王合春营生还者仅70 余人。
也采用了《长城血战记》中,宋哲元的16日开战说。大多内容引用的是前述第二十九军对外的宣传材料,和其汇编的《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一文内容(见39页)。但数字上有斟酌迹象(并未采用歼敌两千之说)。
第三例,邓一民《长城抗战史》(153-155页)
3 月15 日夜,由日军步兵第四旅团(铃木美通)之步兵第三十一联队(早川)、步兵第五联队(谷仪一),附骑兵若干,装甲车多辆,联合蒙鲜伪军两旅,共五六千人,先后到达半壁山一带。
17日 ,“是日午前,日军以步炮联合约五六千人,在20 余架飞机掩护下,向罗文峪、山楂峪发起猛烈进攻”。 “是役激战一昼夜,敌我血刃相搏不下20余次,日军伤亡甚重,其吉田少佐被击毙。刘师除王合春营长、张勋贤连长阵亡外,总计官兵伤亡四五百人”。
“ 18 日午前2 时,侵犯罗文峪、山植峪之日军,复调集步骑炮联合之兵力约3000 余人…”“经罗文峪三天鏖战,日军损失惨重,估计日军兵力由出发时的5000 人减少至3000 余人,日军伤亡大尉以上官佐8 名,内有吉田、早川大佐,已无力发动新的进攻”。 “不可一世的早川支队,遭此重大打击后,军势一服不振,在以后的长城作战中,早川支队已销声匿迹。”
此文几乎完全继承了宋哲元的对媒体讲演,和《长城血战记》,《第二十九军华北抗战阵中日记内容》。以上战史记录,在叙述中都旁征博引,貌似学术书籍,实际也作为权威性的长城抗战学术专著出版。但使用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第二十九军的对外宣传内容。目的也很明显,此类党人编写战史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求真求实,而是站在民族立场上宣传抗战的大捷,胜利。
何谓档案,何谓史料批判,何谓学术研究,何谓政治宣传?可见很多国内的抗战史研究者,出于对所谓的政治立场,党性,民族气节的忠诚,长技、热心于对民族抗战的渲染颂德,相反对学问研究的最基础原则都不能恪守。历史研究者不去研究档案记录,而将宣传中的不真实的糟粕继承下来,并作为事实,写入史书,用于教育,结果更促进了各种误谬的流传。成为今日抗战史记录中的一种病理,通弊。遗憾的是,今日能受到法律保护,成为所谓“国家认同建构”下“民族记忆”一类者,大多都是此类历史垃圾。
[1] 北平军分会《北平军分会阵中日记》,1933年,15页。(《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三辑》第二册所收)。
[2] 前出《长城各口之战斗 》第四章《罗文峪方面战斗经过》,35页。
[3] 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07-061
[4] 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3-409
[5] 北平东方学社《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1933年4月,2页。
[6] 北平东方学社《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1933年4月。
[7] 《长城抗战档案汇编》1-239-241页。
[8] 《长城抗战档案汇编》1-247-248页。
[9] 《长城抗战档案汇编》1-252-253页。
[10] ?《滦东及长城作战》,11页,35页。
[11] 江绍贞《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01-103页。
[12] 余子道《长城风云录》,上海书店,1993年,102-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