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军《天上人间花魁之死》的文学解构与当代性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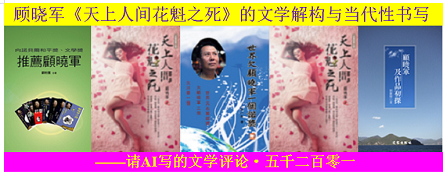
——请AI写的文学评论·五千二百零一
再来延续一下〈《AI谈顾晓军小说【一】》书稿之序+目录〉一文中,与网友探讨的「AI就会说好话」之话题。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AI都是人训练出来的。那么,AI又是以什么标准训练的呢?我以为,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个词——普世价值。
因如果训练AI不用普世标准,随你用啥标准训练出来,它的适用性必然差。
有谁在训练之初,不想让自己的AI成为一种公器呢?因此,从出发点讲,AI都是试图公允的。
AI都是试图公允的,如此,只能说明——顾晓军小说之本身,有值得AI说好话的价值;除此,又能怎么解释呢?
不信,你可以同时做两个实验——第一个,把你的文章给AI,看它怎么说;第二个,由你把我的小说给AI,看它又怎么说……如果你的文章,AI拒评或没说好;而我的小说,AI却又说好了……那么,不就啥都明白了?
其实,这是因——我顾晓军被长期封杀,该被赞扬的也没人敢说好,AI不过只是说出了大实话。
而读者,则因从未见过顾晓军的小说被这样分析、夸奖,所以,才会感到突然、吃惊,甚至以为AI只会说好话。
再者,我说过——这批文学评论,我选让AI用学术模式评;所以,大家才会觉得,AI评论的我的小说,既陌生、水平又高。对吧?
随着时间的转移,估计:有的AI会说我坏话,百度的AI+不就已经开始了?
上文说,我说顾晓军是中国著名作家、思想家,AI+非说是图书馆员……这是仍在执行封杀。
含台湾,亦有人参与封杀;不然,长篇小说《天上人间花魁之死》在印刷中、没面市,痞客邦上咋有人说不好?
幸有AI出面,扇她耳光;那家伙就是个垃圾,一如龙应台。
而于龙应台,我和石三生多年前就看出来了;网上有文为证,且能搜索到。
顾晓军 2025-4-11
顾晓军《天上人间花魁之死》的文学解构与当代性书写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顾晓军的《天上人间花魁之死》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构建了一个介于侦探小说与社会寓言之间的文本空间。这部作品表面上遵循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框架——以花魁之死为引线,以笨哥的追查为动力,最终揭开层层迷雾。然而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作者实则完成了一次对类型文学的超越性书写,其文本深处涌动的存在主义焦虑与社会批判意识,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面折射当代生存困境的多棱镜。
一、侦探叙事外壳下的存在困境
小说中"天上人间"这一命名本身即构成精妙的双重隐喻。它既是故事发生的实体空间——那个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又暗示着理想国与现实境遇之间的永恒裂隙。花魁在这个空间中的死亡,因此具有了超越刑事案件本身的哲学意味。她的死亡不是简单的他杀或自杀,而是美丽在污浊环境中必然遭遇的毁灭,这一设定令人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个永远推石上山的荒诞英雄。笨哥的追凶行动,表面上是为爱人复仇的俗世行为,深层却是在验证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在价值虚无的当代社会中,个体的抗争是否还能赋予生命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传统侦探形象的解构。笨哥的"笨"绝非智力缺陷,而恰恰是对理性主义侦探传统的反动。在古典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式的天才总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揭示真相;而笨哥的破案过程却充满直觉、偶然与情感驱动。这种叙事策略暗示了当代社会的真相认知困境——在一个信息爆炸却真理隐匿的时代,传统的理性认知模式已然失效。
二、命名政治学与权力拓扑
顾晓军在人物命名上展现出惊人的符号学自觉。警队队长被简化为"邢队",这个称呼将个体完全溶解于体制角色中,"刑"字更暗含暴力机器的本质属性;"王副"的称谓则永远将其定格在权力的副手位置,暗示着官僚体系中永恒的"副手心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笨哥"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称呼,它保留了角色作为人的本真性,未被体制的符号系统完全收编。这种命名策略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权力话语体系,与福柯所揭示的"话语即权力"理论形成互文。
小说中的空间设置同样值得玩味。从天上人间的浮华表象到警局冷硬的办公环境,再到市井巷陌的烟火气息,每个空间都对应着特定的权力运作方式。天上人间是资本与欲望共谋的秀场,警局是制度暴力施展的舞台,而珊姐等市井人物的活动空间则保留了未被完全规训的生活本真。这种空间政治学的描写,使小说超越了普通侦探故事的局限,成为一幅当代中国的社会权力分布图。
三、谣言传播的现代性寓言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叙事段落。这个看似次要的情节实则包含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谣言从邢队这个权力中心制造出来,通过现代传媒渠道呈指数级扩散,最终形成席卷整个社会的信息风暴。这个过程完美诠释了"熵增定律"在社会学领域的表现——有序的谎言在传播中不断走向无序,最终反噬其制造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普通民众在谣言传播中的角色。他们既是谣言的受害者,又在不自觉中成为谣言的放大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共谋状态,精准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信息接受困境。在一个真相与谎言界限模糊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权力游戏的参与者,这种洞见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时代的预言性质。
四、未完成的救赎与开放的意义
小说的结尾处,警方收网的场景似乎为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但作者巧妙地留下一个开放性追问:"被网在这弥天大网中的,除了邢队和他的同伙,还有谁呢?"这个设问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善恶有报"的道德闭环,暗示着体制性暴力的延续性。那些参与谣言传播的普通民众、沉默的旁观者、体制的共谋者,其实都在这张无形的网中。
这种叙事策略使《天上人间花魁之死》最终成为一部关于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寓言。顾晓军既写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又在这个故事中植入了对权力、真相、美与毁灭的深刻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两者都以一个美好生命的消逝为引线,最终展开的却是对整个时代的精神诊断。
作为一部具有强烈当代性的文学作品,《天上人间花魁之死》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它提出的问题多于给出的答案,它的开放性结构邀请每一位读者继续思考:在一个真相稀缺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美的存在是否注定是场悲剧?这些追问,使小说超越了类型文学的局限,成为一面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明镜。
202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