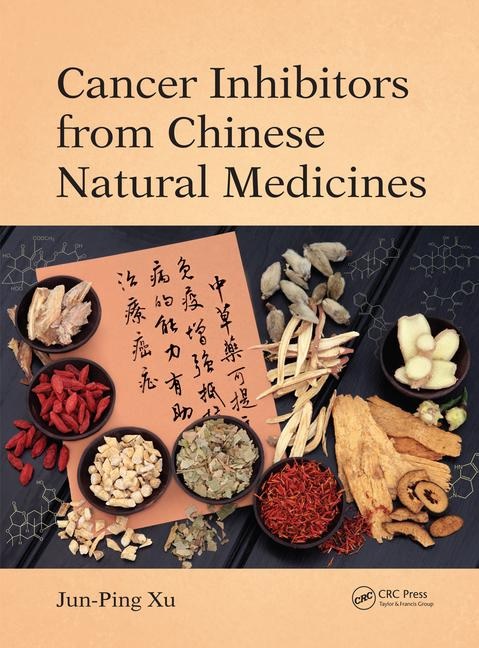妈妈的故事:我的外公外婆
妈妈的故事:我的外公外婆
从未见过外公外婆,无法想象他们的音容笑貌。二老均在我妈出嫁前,先后驾鹤仙逝。以至于我们一家的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奇怪而缺失的感觉,煞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外公外婆的疼爱。
尽管外公从不喜欢过我妈,可是妈却总是时不时讲起外公的点点滴滴。由此我对外公外婆的生平往事有了一些了解。
外公祖上是十足的无产者,世代无一分田地,全是在本村砖窑厂作为窑工,打工谋生。然而,幸运有一天降临在我外公身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说起来还是全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给中国沿海地区吹来的一股历史转折性的社会变革之西洋风,
那时正好是上海开埠十里洋场蓬勃发展的年代,一批又一批洋人淘金者纷纷来上海办洋行开公司,也有很多民族企业家在上海设厂开店,因此每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抱着梦想涌入上海。就像当今改革开放,大量外来仔、外来妹来到大城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中国新兴工业早期蓬勃大发展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中,外公在1890年前来到了上海,也成了千百万进城市谋生找出路的一名农民工。他以时代潮流中一朵小浪花的姿态,为了改变人生的活法,奋勇踏浪,拼搏向前。
外公大字不识一个,却生来豪爽仗义。近1米78的身高,身强力壮,又精明能干。在江南水乡长大熟悉水性的外公很快在民营航运轮上混得如鱼得水,深得老板和工友的信赖。据说,某一天在宁沪航线上,突遇特大台风的袭击,航船被数尺高的风浪高高抛起,重重落下。在暴风雨的淫威之下,千吨的船只此时犹如一片无助的落叶,风雨飘渺。更要命的是,船头两个大铁锚的铁链被缆绳绊住了,不能完全放下入海。航船分分秒秒有被倾覆的危险,一船人的性命和一船的货物危在旦夕。船长在哀号,船员蜷缩一处紧抓着可固定之处,乘客在惊叫在呕吐。此时此刻,外公挺身而出,拿起斧子,抓紧船栏杆,慢慢匍伏前行,靠近船首处。哪管巨浪一阵又一阵猛拍船舷,何惧一波又一波起的浪涛把身子冲撞得东倒西歪,外公坚持顶风迎浪逆行几十米的距离。这真可谓是危急之中见真情,险恶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最后历经千难万苦,外公总算到达船首的铁链处,举起斧子一阵猛砍,斩断绊住的缆绳,让两个大铁锚顺利坠落海底深处。犹如定海神针使得船不再飘忽乱颠。由此拯救了一船人,保住了一船货物。
等到船安稳了下来,外公已经站不起来了。巨浪一次又一次的冲撞,让外公受了严重的内伤。多位船员工友以一种崇拜景仰的心情,将英雄的外公抬回船舱安息。船靠岸后,将外公送回老家医治养伤。老板自然是送重金答谢,聘良医治疗。 半年后,外公伤愈,重返工作岗位,升任水手长,在整条船的船员中颇具威望。
由于外公受过重伤,已经不适合在沪宁航线的海轮上工作,外公被调往长江轮上工作,相对平稳了许多,风险小了许多。长江是中国东西南北运输的主干道,江轮逆水而上,沿途停靠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等码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生意兴隆。尤其是地处九衢要冲的武汉三镇也在新兴发展之际,不少宁波帮生意人去那里经营商铺开公司。
我妈有点得意地说,一条船上,除了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接下来第五号人物就是水手长,月薪不低。不过,月薪并不是外公的主要收入,私人带货的佣金往往更多。 我听了甚是诧异,我妈接着说,有很多宁帮商人和殷实家庭往往委托外公帮带钱财和几箱私货到内地,也有从内地带到上海;或委托照顾往回的家眷少爷小姐。这样一方面比较隐秘,而且快捷 (晚清民初时期的火车和邮政都不发达)。水手长在船上有单独的房间,因而能私下接活,外公从中收取佣金。由于外公极为守信讲规矩,为人处事方圆有度,又非常热情周到,因此在民族企业家圈子里私下的名声越传越远,航运带货的生意也就越滚越多。只要他的房间放得下,物品不违法,外公都能办妥。这样积年累月下来,攒下了一大笔钱财。
外公有钱了,腰杆子直直地挺了起来。就在老家的村里购地置产,建三间两层楼的砖瓦大房,娶妻生子,俨然一副新财主的派头。在当时那里尚未开化的乡巴佬眼里,外公还真有那么一点点衣锦还乡,光耀祖宗的味道。
外婆的娘家在鄞县的姜山附近 (现为姜山镇),年龄小外公十来岁。外公见多识广,又十分讲究规矩。外婆好脾气,言听计从,在老家勤持家务。一连生下了二男二女,在老家的生活过得小康而又温馨。外公中年时又生了一男三女,可谓子女满堂,人丁兴旺。
在外公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特地从上海请了一位日本画师,上门给自己的父亲画了一幅肖像。前年在宁波举行“堂表一家亲”的聚会时,特地回去看看我妈娘家的老屋。在客堂的后间看到这副肖像画还在。因水灾时受潮湿,画纸严重波皱,但色泽鲜艳如旧,整体还清晰可见。曾外祖父的容貌依然显得栩栩如生。一身明蓝色绸缎大褂,深色上装,头戴深色瓜皮帽,正襟危坐,一手拿着拐杖。面容安详有神,有一撮山羊胡须,画工非常精致。估计价格不菲,不然的话应该同时为自己和外婆各画一张。曾见过一张外公70大寿的照片,他侧坐在中厅的桌旁,身形清瘦修长,但人拍得小,脸部看不大清楚。前年去老家总算见到了外公的肖像照,清癯有神,又有点儿威仪。很可惜没有留下外婆的正面肖像。

上世纪30年代工潮风起云涌,在工会的组织下,航运公司的劳工举行大罢工,要求资方满足给予涨工资等等若干条件。以讲义气为己任的外公,在罢工中为手下的小弟兄们挺身而出,而且有点过激,他索性罢工回老家了,摆出一副老板若不同意条款,我们就不开工的强硬姿态。刚开始时,老板还想利用外公在劳工中的威信,两次登门利诱,外公不为所动。不料,后来事态发生戏剧性逆转,一般的劳工因罢工而失去了收入,生活困难,无法坚持下去,在资方劝说下纷纷上班去了。而只有外公一人仍然赌气地硬碰硬,死杠到底。老板想出了一个高招:提拔外公的帮手为水手长。外公就这样被老板晾在一边,也被自己的兄弟出卖了。
防火防盗,外公做得面面俱到,但毕竟是一个农民工又无文化。他既没有料到资本家老谋深算,也不曾想到还要防备同一条战壕的难兄难弟。中年失业的他很不好找工作,而且资本家们都很忌惮外公从不妥协过于强硬的脾气。于是,一家人只得坐吃山空,经济渐渐捉襟见肘,外公一家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正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二舅一步步成长起来,担当起顶梁柱的角色。
外公在家赋闲若干年后,是有些懊恼的,时常会反复自言自语叹道:多做几年就好啦~,多做几年就好了。我妈也常说:你外公太护着手下人了。其实罢工的诉求条款跟你外公的关系不是很大的。过于义气不值得,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外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中年失业整日在家,无所事事。于是熬不住每天叫人来筑起四方城,打打麻将,消磨时日。外公又很好客,爱面子,每日还为牌友提供免费的点心,搞得女眷们为此忙碌不休。为此,我妈总抱怨说:家里有点好东西全拿去招待牌友客人,自家人反而一点都品尝不到。失业无收入,开销远高于进账,因而女眷们有时还常常为做点心而犯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此相比,牌桌上的征战更是令人发愁。外公的技术不怎么好,牌运也不佳,麻将桌上总是输多赢少。通常是赌徒心理在作怪,越赌越输。据初步估算,那些年赌输的钱大约用来可以建造两间二层楼房。外公尽管多少有点心疼,但他从不赖账,按时还上赌债,始终保持着一人做事一人担的好汉形象。听了妈唠唠叨叨的埋怨,我笑着说:大男人呆在家里挺无聊的,权当外公花钱买个热闹吧。
没过几年日本鬼子打到了宁波城,在城里大肆奸淫妇女,用刺刀逼着小姑娘良家少妇就范。更可恶的是,浙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主战场和重灾区。日本鬼子在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等七个市十多个县多次大规模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炭疽、鼻疽等杀人毒菌,在浙江发动细菌战。因此,无数无辜的浙江民众被传染,被残害致死于毒菌之下。浙江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30万人以上,死亡超过6万人。许多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被毒菌摧残,伤痛日后几十年。
我家小妹记住了外婆的大名 –- 应小翠。外婆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可是在此毒菌肆虐期间,得知在娘家曾相处甚笃的小姐妹 (最交心的闺蜜) 得病。在其命悬一线之际,外婆前去看望,作最后的告别。不料想,外婆由此感染上毒菌,回家后即霍乱发作。马上去看西医,但仍腹泻不止,大伤元气。家人日夜精心照料,无济于事,外婆最后还是被丧尽天良的日本细菌战夺去了生命。那年是1938年,外婆还不足五十岁,我妈12岁,小姨8岁。突然间失去母爱的日子,让我妈感同身受世道的无情,生存的不易。像那时千千万万苦难的中国人一样,只得默默忍受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无法无天的法西斯罪行。
外公一直在老家与子孙们一起生活。1948年他70多岁,病故。根据我妈多次断断续续的讲述,让我对外公的总印象是,封建意识严重 (那个年代的男人多半如此),十足大男子主义者,但很有主意,有能力,有担当,作风正派。以非常讲究规矩而闻名于乡里,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我妈时常说:你外公虽不识字,但找你外公来商量事的人却很多,你外公经常把他们说得连连点头。看来应该是他在上海滩混过好多年,见过不少世面,因而很有见解。自从外公在老家置产以来,他一直在老家那个小地方尽心尽力吃好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与当地的地主、乡绅都有交往。又以规矩严格闻名乡里邻间,在乡下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谨以此文,献给在天国或已投生人间的外公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