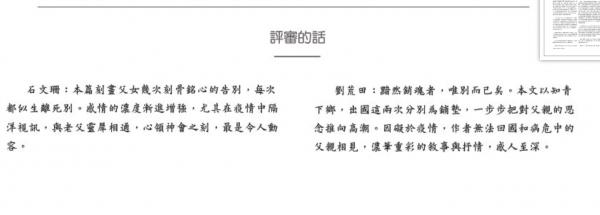与父亲告别
【百草园】这篇文章获得2021年汉新文学散文佳作奖。刊登在这个月的汉新杂志上。在此感谢评委的厚爱,同时也感谢汉新这个文学平台。
我的父亲,今天仍然躺在医院里。也许,上天会给我机会,让我们可以当面话别?

无论中文英文,告别(farewell)与再见(goodbye)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天天跟家人说再见,但不可能每天和周围的人告别。告别,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分别。而且,在这世上,有一些告别,可能会成为永别。
尽管告别有着特殊意义,可是每个人的一生中,还是会经历很多次的告别。迄今为止,我跟父亲就有过若干次的告别。而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的,有几次。
第一次与父亲告别,我十七岁,时逢文革末期。那时中学毕业的我,没有任何选择地被政府,送到农村去,去当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时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让父母们都挖空心思地想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城里。记得父母也曾经费尽心思地挣扎过。一开始,不知道父母从什么地方听说,高度近视可以留城。因为我有轻度近视,父母就让从来不戴眼镜的我,天天戴眼镜,同时他们找门路,送礼物。非常不幸,我的近视度数太低了,无法达到留城的标准。于是父母调转方向,希望我可以参军。我被带到一个从未谋面的亲戚家去求情,那亲戚为难地告诉父母:门子不够硬,参军的希望不大。就是挤进去了,也只能在医院给首长们端尿盆。
离家的日子渐渐逼近,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那天,父母倾其所有,为我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父亲一直陪在饭桌旁,不停地劝我多吃,好像此刻女儿多吃了,就可以抵挡后面农村带来的饥饿。结果,我们磨磨蹭蹭,让我成了最后一个登上送知青客车的人。在我登车的那一刻,父亲忽然脱口而出:鸿儿(我的乳名),希望你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也是第一个回城的!闻言回首,看到的是,父亲眼里深深的担忧。就这样,带着对前途的恐惧和迷茫,面对着父亲痛苦焦虑的表情,我和父亲有了第一次难忘的告别。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告别,我已结婚生子,那是1989年的7月。这次,我要带着牙牙学语的女儿,远赴万水千山外的美国,去和在那里攻读博士的先生团聚。是父亲,一路相送到北京。机场里,父亲一直殷殷叮嘱:事事要小心,照顾好自己,美国是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在那里安全第一。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恐惧的不是美国,而是一个无法说出口的疑虑:这是不是永别?这样想,不只因为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年前出国留学的先生,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出国几个月后,已然撒手人寰。而就在一年前,公公也曾亲自送别自己的儿子。与今日父亲的送别相比,此情此景何其相似,怎能不让人心惊!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父亲的手,想把他也带到美国。
十里长亭相送,终有一别。出关的时刻到了,抱着女儿,我已泪流满面,不想让父亲看到我的眼泪,一直不敢回首。感觉后背有一种火辣辣的刺痛,我知道那是父亲不舍的目光。那一刻,心里那份苦楚,那份惶恐,那份不安,应该是父亲和我的共同感受。在我就要消失在父亲视线里的那一刻,听到父亲在背后高喊:“鸿儿,不要担心我们,不要回来,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心头一颤,父亲竟和我一样,想到的也是永别!
时间飞逝了几十年,经历了那么多人生的变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是幸运的,因为上天允许我在祖国和美国之间自由往返,让我得以年年与父母相亲相聚。直到庚子年的降临。
庚子伊始,随着疫情的发展,心里开始隐隐不安,曾经默默地对着苍天祷告,请保佑父母,让他们平安。
可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庚子年的九月份,父亲昏迷进入医院急救。接到消息后,头脑是一片空白,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虚无那么不真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赶快回国,回到父亲的身边,伴陪年近九旬的父亲,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程。 泪水涟涟,心里狂呼:父亲,请您等一等,等女儿回家,等女儿飞到您的身边!
因为所有华裔的十年签证,都暂时失效。收到父亲病危消息的当天,就给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发去电邮,题目是:“父病危,恳请帮助!”
当时,一面应付领事馆的各种手续要求。一面心急火燎地了解目前的回国限制。赫然发现,外籍华人回国的路,变成了一架难以攀越的天梯。在我们面前忽然出现了各种要求,要过五关斩六将,才有可能踏入国门。外籍回国,一定要有中国领事馆签发的“人道签证”;要定购国家要求的“五个一”航班的机票,当时的机票至少要排队到两个月以后,因为“五个一”是指:一航司一国家一航线一星期一航班,这表明没有几班可以飞往中国的飞机;登机前要做新冠病毒的双检,检测地点最好是领事馆指定的,检测结果需要领事馆批准登机的绿码;飞机抵达中国,你要在落地地点隔离14天,当时还了解到,我的家乡沈阳,还要求另一个14天的居家隔离。越看越觉得父亲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心头狂喊,父亲,请您一定等一等,给我时间,让我有机会跟您话别!
急切地跟家人请求:希望能与父亲的主治医生对话。一跟医生通上话,马上告诉他:我在美国,最少需要4周时间,可以登上飞机,按中国目前的隔离政策,回国后还需隔离4周,您能不能让我父亲坚持两个月?电话那端,医生为难又委婉地说:如果需要两个月,您就不用回来了。要知道,您父亲目前处于昏迷休克状态,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病因。而且,以他的年龄,我们很难做出什么保证。
我的心瞬间沉入深渊,什么?父亲只有不到两个月的生命了?!那一刻,忽然警醒,难道,今生今世,我和父亲没有机会做最后的告别?!
那些日子,午夜梦回,总是梦见父亲。梦境里,父亲在为生病的我熬药;父亲在为我补习高考;父亲放弃自己的事业,远赴美国为我们照看新生的儿子。也有很多次,梦见的是,父亲在渐渐远行,而我在后面拼命地追赶,父亲,等等,请您等一等,女儿,女儿还有很多话要跟您说……
也许是父亲听到了我的呼唤,也许是上苍回应那么多亲友的祈祷,几个星期后,父亲居然从昏迷中醒来。医生还是警告:老人不能自主呼吸和进食,没有能力与他人交流。但,父亲毕竟不是在昏迷状态了!抓住这个上天赐予的机会,我要争取,要尽快赶到父亲的身边。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出来阻止我回国的,居然是家里的至亲。家人拒绝给我领事馆办人道签证要求的证明--父亲病危病重通知书。不理解和绝望,让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焦虑愤怒中的我,几乎夜夜无法入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知道吗,这是拿走了我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家人也是分了两个阵营。母亲,她害怕我会路上染上病毒,不想在送别自己丈夫的同时,还要送别女儿;弟弟一家,则是一种无奈的自保。因为,如果我回去,如果我又带入了病毒,他们可能会丢掉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
从今年开始,时不时与父亲视频相聚。镜头里的父亲,枯槁瘦弱,身上插着许多管子,睁着双眼,无语无声。我的心在滴血在流泪,父亲,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您,我知道您一定非常痛苦非常无助。可还是要强打笑脸,对他说:爸,是我。我们都好,您不用担心。您要多多保重,我会争取去看您。镜头那面,父亲只是看着我,依然沉默无声。我又说:爸,您听见了吗?知道是我吗?知道的话,请您眨一下眼睛,就一下。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瞬间,父亲,父亲他竟然深深重重地闭了一下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的眼泪完全不能控制地涌了出来。
父亲,父亲,我挚爱的父亲,我没有料到,我们人生最后的告别会是这样。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数,也许这是上苍的安排。父亲,父亲,我们是要生生世世做父女的。这一生,我们没有最后的告别,我们也不要最后的告别。不相别,就是常相见。父亲,父亲,我们说定,没有告别的今生,就是互相许诺的来生,您还是慈父,我还做乖女。父亲,父亲,我们的父女情缘,不会因为您的离别而中断,您对女儿倾注的父爱,将会伴随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