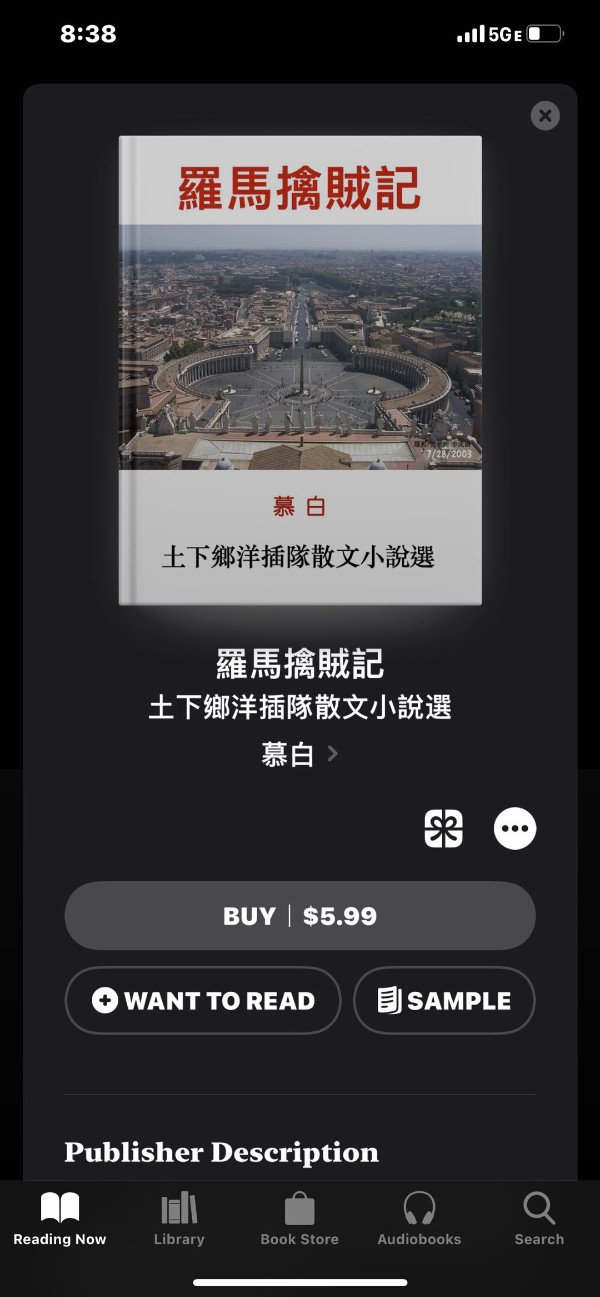化肥廠的槍聲
正是“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時候,我一個人回到了黃河岸邊的故鄉。
少年時候就獨自出外謀生,很少回過故鄉;如今海外飄零不覺也已經三十多年了,更難有機會返鄉祭掃祖宗廬墓,所以這天下午不知不覺地竟在父親的靈前坐了很久。等到我站起身來,這才發覺天色已經快要暗了下來,偌大的一個陵園內幾乎沒有了人蹤,只有瑟瑟的雨聲和三兩點昏黃的燈火在黑黝黝的林木深處閃爍。我心底忽然生出了一種沒來由的惆悵,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請問,您可是......詹望?”剛剛走到松林間的小徑轉彎處,一個女人低低的聲音忽然在我的身後響起。我吃了一驚,急忙轉過身來。
一個胖胖的坐在輪椅上的陌生中年女子正專注地望着我。我竭力地在記憶深處搜索,可是徒然。她怎麼會知道我上中學時候的名字?就算知道,又怎麼能夠認得出我?海外的風雨無情,這些年來的苦鬥掙扎,使我變了很多。有時拿起過去的照片,真怕看到那個穿一身紅黑相間的運動服,雙手高高捧起獎杯,滿臉笑容的年輕人。歎息聲中常常連我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來了,可她……
“我是夏紅,你的中學同學。這麼多年不見,你一定忘了我吧?”她用雙手輕輕把輪椅搖近,繼續目不轉睛地看着我。
“啊!夏紅,真地是你!?”我的天!她怎麼也變得這麼老了……我臉上的表情一定泄露了心裏的秘密,她的嘴角隱隱地閃過一絲苦笑。
“我變得太老,太醜,讓你都認不出來了,是吧?”
“……”我有些遲疑,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這麽多年過去了,她還是這樣,說話從來不給人留有一點餘地。然而,人,畢竟是不一樣了。仔細看看,她的臉上早已失去了光澤,曾經是如雲的兩鬢也出現了幾絲灰白。也許,她的眉眼深處隱隱地還殘留有一抹過去的影子,只是,那個愛穿一襲白色的連衣裙,無論走到哪裏都最引人注目的美麗少女哪裏去了?
“我早就看出來是你了,可是怕打擾你,一直默默地坐在一邊等着你。”她向左側微微仰起臉,一邊看着我,一邊輕輕地用右手向後掠了一下長髮。她這樣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忽然勾起了我太多,太多的回憶。當年在學校裏,面對着我們這一群無比仰慕她的毛頭小夥子們,她常常就是這樣,臉蛋微微仰起,半真半假地像個高貴的公主一樣斜視着我們,不時把眼前那垂下來的一縷長髮用右手向後掠去。而我們爲了引起她的注意,哪一個不是用盡了心思?人的記憶真是奇怪。剛剛我的腦海裡還是一片空白,可是隨着她那輕輕地向後一掠長髮,一下子那些幾十年前的往事竟然如同打開了閘門的洪水,肆意地四處泛濫而一發不可收拾……
她曾是我們學校裏最漂亮的女孩,兩次全市中學生體操比賽的高低杠和平衡木冠軍,更是我們這些校運動隊男生眼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記得那時我們都是懷着敬畏無比的心情,仰望着長髮飄逸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從領獎臺上輕盈地走下來的。她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常常就是像現在這樣,不經意地把眼前那垂下來的一縷長髮用右手向後掠去。這個掠發的動作是那樣的輕盈,優美,簡直就像她剛剛在高低杠上表演了一連串複雜動作之後騰空落地,伸直右臂向觀眾致意時一樣令我們着迷。文革開始後,她因爲能歌善舞被拉進了一派紅衛兵辦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很是風光過一陣子。六七年武鬥開始後,我躲得遠遠地當了逍遙派,她參加了那派紅衛兵的救護隊,聽說她在本市最慘烈的那次化肥廠大武鬥中受了傷。以後我就下鄉了,再後來又到了外地上大學,剛剛畢業我就出國留學了,從此再也沒有聽說過她的消息。
“你……你這些年來還好吧?”凝視着她那由於缺少陽光而顯得蒼白失血的面龐,還有臃腫得變了型的身材,我好半天也想不起來該說些甚麼才對,只覺得心裏面湧起一陣一陣的寒意。
“好?哪裏說得上,可死吧,又不甘心,所以只好這樣槁木死灰一般地活着。”她輕輕歎了口氣,剛才見到我時的一絲喜悅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一雙大而無神的眼睛裏也起了一層霧。此時此刻,她臉上那種悲哀的神情真讓我恨不能立刻轉身跑掉。
“今天,你……你也是來掃墓的吧?”終於,我沒話找話地問。
“是的。”
“給誰掃墓?”
“……”她遲疑了一下,沒有回答,只是不停地用手擺弄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大信封。過了好一會,她似乎下定了決心,從信封裏抽出了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遞給我。我接過看了一下,似乎有些面熟,可一下子又實在想不起來是誰。我望着她,有幾分茫然地問道,
“這是……”
“這是十五中的賀耀武。怎麼,不記得了?就是那個瘦高個子,六五年在全區運動會上打破百米紀錄的……”
對了,一點不錯,就是賀耀武,就是他。那個很高,很帥的男孩。他本名叫賀沛文,文革中追隨潮流改名爲賀耀武,爲的是表示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聽說還親自帶領紅衛兵抄了他父母的家。
就是賀耀武這小子,文革前憑着他那一身健美的肌肉,還有一張專門會討女孩子歡心的巧嘴——也有人說主要還是他那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的優裕環境——終於獨占鰲頭,贏得夏紅的芳心。那時我們六中這一幫代表隊主力的男生嘴上不說,可心裏個個都恨透了他。要知道,十七八歲可正是人生感情最豐富的時候啊!而他,竟敢把我們學校最迷人的姑娘搶走了!想到了這些,我不免還懷有幾分妒意地問道:
“賀耀武他人現在哪裏?”
“就在前邊,朝右一拐就是。”她幽幽地說。
“他和你一起來掃墓了?”
“不,不是,他……他……一直都在……在……這裏。”
“什麼?在這裏?你說的什麼?”我摸不着頭腦地問。
“走,我帶你去看看他吧。”不等我答話,她已經用雙手搖動了輪椅。我趕緊跨上一步要推她,她卻搖搖頭,我只好默默地跟在她後邊。
蒼茫的暮色中,她在陵園角落裏一片小小的草坪上停住了。綠盈盈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齊齊,同四周灰色的殘牆斷垣顯得極不協調。一塊小小的石碑立在草坪中央,後面是一個顯然新修過的墳頭,墳的旁邊是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松樹,茁壯的枝葉上滿是亮晶晶的水珠,空氣中充滿了松樹特有的清香。我滿腹狐疑地走近墓碑,蹲下來,發現粗糙的石碑已經開始斷裂剝落了。我掏出紙巾擦乾上面的水跡,這才勉強看清那已經有些模糊了的碑文:
紅衛兵造反總部戰士賀耀武爲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化肥廠戰鬥中英勇犧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1967年8月18日
我有些不敢相信地扭回頭去,看到的是夏紅滿眼盈盈的淚光。她從輪椅上俯下身去,輕輕地掐掉墳上的一株枯草,小心地放進衣袋裏,半天沒有說一句話。
“真沒有想到,像賀耀武這樣的人會死在武鬥中。”我歎了口氣,慢慢地立起身來。“聽說他的出身並不好,他怎麼會參加了紅造總,又怎麼會被打死了呢?”
“唉,說起來都怪我……”她的聲音有些嗚咽起來,“要不是我跟他好,可又嫌他的出身不是紅五類,他也不會和家庭徹底決裂,更不會去參加紅造總……”
“參加紅造總也不一定非要去武鬥啊。”我當年是個逍遙派,因爲早就看穿了那些謊言和愚弄,是決不會去爲他們賣命的。
“這些事說起來話就長了。”她用手慢慢撫摸着小松樹的枝葉,仿佛那就是她的愛人的化身。“他愛我愛得那樣深,爲了我他沒有不能做的事情。其實他參加紅造總只是爲了能夠和我在一起,我……我那時可真的是太傻,也太天真了。爲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什麼都豁出去了。我沒日沒夜地到處參加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說,連武鬥的時候,還非要跟着宣傳車上火線不可。
“我永遠也忘不了六七年的八月十八日。那一天,是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的一周年紀念日。那天上午,我們和別的學校的造反派聯合舉行紀念接見紅衛兵的大游行。沒想到隊伍剛剛走到保守派紅色赤衛隊的大本營,化肥廠的大門前,裏面就沖出一群手持長矛大刀的赤衛隊員。他們二話不說,見到紅造總的人就用大刀亂砍,用長矛亂刺。我們的隊伍一下子炸了營,當場就死傷十幾個人。
“混亂中賀耀武他們保護着我們這些女生逃回總部。下午我正在幫忙救護傷員,聲援我們的工人造反派大部隊忽然來了,本來已經潰不成軍的我們立刻士氣大振。賀耀武他們那些男生本來早就殺紅了眼,當時立刻就要跟着大部隊前去化肥廠討還血債。我見攔不住他,就乾脆和一些女生組成個救護隊跟着出發了。
“你知道化肥廠位於城外,工廠四周本來全是齊胸高的玉米地。赤衛隊怕遭到我們突然襲擊,早就把圍牆外面五十米以內的玉米全砍光了。到了地方,我躲進停在一棵大樹後面的宣傳車裏,眼看着賀耀武他們端着長矛沖向化肥廠的大門口。當時誰也想不到的是,化肥廠這樣大型企業的武裝部倉庫裏存放有大量的武器彈藥,赤衛隊裏更有不少是轉業軍人,其中還有一些是神槍手!
“我們的人還沒有接近大門,躲在化肥廠大樓窗戶後面的赤衛隊就開始射擊了。盡管這樣,賀耀武他們還是憑藉人多沖進了大門。就在這時,樓頂上響起了“噠噠噠”的機關槍聲音,我們的人立刻倒下了一片,其餘的人被迫退了出來。遠遠地我眼看着身穿紅背心的賀耀武就要跑到安全地帶了,吊起的心剛要放下,沒想到一颗子彈追上了他,只見他兩手一仰,栽倒在地上。
“我當時也不知哪裏來的那麼大的勇氣,抓起了一個急救包,跳下宣傳車就朝他飛跑過去。雖然子彈“嗖嗖”地不停從耳邊掠過,我還是沖到了他的身邊。我跪下一看,他大腿上中了一槍,鮮血染紅了綠色的軍褲,又一滴一滴地滲進了他身下的黃土地。我草草地替他包紮了一下,然後吃力地背起他,一步一步地朝自己一方的陣地移動。沒走出多遠,又是一顆子彈從後面擊中了他。我當時只聽見他“啊”了一聲,兩個人就一起摔倒在地。等到我們的人拼死把我們倆拖回到大樹後面,才發現那同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身體,又鑽進了我的脊椎骨裏。
“還沒有送到醫院他就死了。我的脊椎神經則受到了嚴重傷害,下身從此完全癱瘓了。你知道嗎?那顆子彈至今還留在我的身體裏,每逢陰天就疼得鑽心一般。唉,就這樣,我和輪椅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些年來,只有這裏是我最常來的地方,因爲只有在這裏,我才覺得心裏有片刻的安寧。你瞧,這棵松樹是我在他下葬的那一天親手栽下的一株幼苗,現在已經長得和他一樣高了……你說,他要是還活着,額頭上恐怕也該和你一樣出現不少皺紋了吧?”
“也許,也許……是吧,”我惶惑地回答。
“可惜他就這樣死了,死了……”她又開始嗚咽。我難過地看着她,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沉默了好一會,我才說:“不管怎麼說,他總算是爲了自己的理想死去的。他若有靈魂,也會——”
“哈哈,靈魂?他若真地有靈魂,只怕要……哈哈……”她近乎歇斯底裏般地大笑了起來,連附近樹梢上的幾只倦鳥都被她的笑聲驚動了,撲楞楞地飛到了半空中一陣亂叫,倒把我更嚇了一跳,心裏越發不自在起來。等到笑夠了,她又直直地盯着我說:“你知道嗎?他死了還沒有幾個月,毛主席就發出了最新指示,說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各派革命群眾組織應該進行革命的大聯合……”
“這個我知道。”
“可你不知道的是,沒過多久,在軍宣隊的指揮下,紅造總和赤衛隊就進行了大聯合,兩派的頭頭中有不少人都進了新的革委會。他們個個都忙着分權,分房,給鄉下親屬辦戶口進城裏安排工作,哪裏還有人管我們這些人?更別提那些死去的人了!到了如今,他們更是當官的當官,經商的經商,出國的出國,沒出國的人也差不多個個都是豪宅名車,小秘二奶跟着到處風光,他們……他們中間……還有誰記得當年化肥廠的槍聲?”
她越說越激動,呼吸也越來越急促,蒼白的臉上竟出現了幾分淺紅。
終於,她稍稍喘了口氣,然後又是那樣直直地望着我說:“你說說看,這個世界爲什麼這樣不公平?我一直在注意着你出國後在本地報紙上連載的那些介紹美國生活文化的文章,可從來沒有看到過一篇關於文革,關於武鬥的,更沒有關於賀耀武和我們這些人的文字。比起我們來,你算是見過世面的人了。你說說看,難道我們的血就這樣白流了?我們寶貴的青春和生命就這樣白白被糟蹋了?”
“這……這……”面對着她錐子一樣尖銳的目光,我真地又一次無言以對。她當然應該知道,中國現在流行的是向前看,向錢看,這就意味着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看看巴金老人,他呼籲建個文革博物館,多少年了都沒成功,耗資巨大的國家大劇院,奧運會亞運會大學生運動會體育館倒建了一個又一個。再說,就是我寫了關於文革和武鬥的文章,哪一家報紙或出版社敢用?我正要把這些意思告訴她,陵園的管理員走了過來。他一臉不滿地說:“這裏關門的時間早過了,我看你們有話還是到外面去說吧。”
我有些如釋重負地點點頭,下意識地又要伸手去推夏紅的輪椅,她卻堅決地搖搖頭,自顧自地朝大門口搖了過去。我只好默默地跟在後邊,一路上我們誰也沒有再開口。
外面的大街上早已是燈火輝煌。她停在“熱烈慶祝黨的九十歲生日”的巨幅標語牌下面朝我擺了擺手,我看見她要走,連忙說:”咱們這麽多年不見,今天一定要好好聊聊。走,我請你去吃個飯好不好?”
“謝謝了,”她搖搖頭,“我實在沒有心情。說實話,這些年來我一直躲着所有的老同學…… 吃飯的事就改天吧?”
“可是,可是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望着她蒼白的臉龐,失去了說下去的勇氣。好一會,我才喃喃地好像問她,又好像自語地說:“爲甚麽呢?這到底都是爲的甚麽呢?”
“因爲我……我怕看見他們就會想起耀武來……今天沒想到竟會在這裏碰到了你。我本想悄悄地走開,可不知道爲甚麽就好像有一只手,硬是把我拽到你的旁邊。”她的聲音哽咽了,用兩只手捂住了臉。一刹那間,我腦子裏閃電一般掠過了一幅畫面,我想起來了,文革之前那一年的全市中學生體操錦標賽的決賽上,她不小心失去平衡從平衡木上摔了下來,當時她也是這樣雙手捂着臉哭泣……多少年了?我低下頭問自己。差不多四十多年了吧?我們短短的人生中又能有幾個四十年呢?
她終於仰起臉來。滿眼的淒愴,滿臉的無奈。她一字一頓地說:“ 詹望,謝謝你陪了我這好半天,再見了——假如我們還能再見的話。”
她揮揮手,搖動了輪椅,走了。
我獨自一人站在那裡發愣了好半天,才慢吞吞地转身朝酒店的方向走去。不遠處我經過了一個歌廳,玻璃大門裡面傳出來一陣又一陣響亮的紅歌聲,“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03/16,2012
04/2021 选自 《羅馬擒賊記 —— 土下乡洋插队散文小说选》, Apple Book Store, 2021
苹果网上书店搜索本书方式如下:
Title; luomaqinzeiji ; Author: mubai ( 慕白 ); 更多订购本书详情请点击: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k3NT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