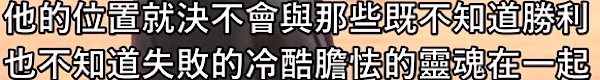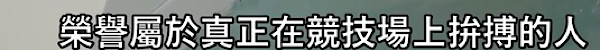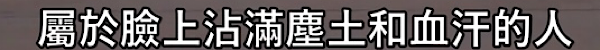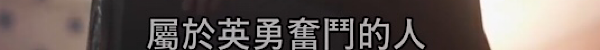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白熊的博客在回复“体育老师”评论“能正面评价上山下乡,少有”时,为他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辩护说:
【其实我对上山下乡的评价不能说是正面评价,若是正面评价就有肯定的意味。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又是绑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的。既然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上山下乡接续着文革,我不得不把我们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我认为这样才是客观的。】
你说“把我们(注:这里你能代表谁?)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一部分,上山下乡与文革怎样分别对待?你又说“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分别对待”就是说“上山下乡”不是“灾难”咯。你的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就是为上山下乡作“正面评价”的,这是非常客观的评述。
白熊的博客还说:【在油管上只要打入很容易找到演出的视频。那么多人的激情演唱能不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首先在油管上看《岁月甘泉》的,最多一个视频观看人多于1万人。其次台上160多人的激情演唱岂能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呢? 这些少数人想代表“绝大多数”,也不是太好代表的。
在这里,不赞同“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博文为上山下乡辩护,不是什么个人“历史积怨“,或者对那段历史“至今耿耿于怀”。《岁月甘泉》把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悲惨世界》唱成了像“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一样的歌功颂德,它能代表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唐燕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你的成功能够代替那些1979年无数的云南卧轨知青吗?
下面转发作者:唐燕在《共识网》上一篇评论。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作者:唐燕
最近歌颂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活动不少。
7月1日“由国家、省级层层审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亲自把关”的北京鸟巢“知青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所展示的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贺卫方)。
7月11日《环球时报》上《知青一代的积极回忆值得尊重》一文承认该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性的记忆”,直言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显然不能划等号”。
早在201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上山下乡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一文,对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自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深圳、北京、香港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地巡演,就在9天前的7月11日又于德国法兰克福“隆重上演”。
《岁月甘泉》的演员多是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知青,他们说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穷,但很少有怨恨;演员中也有“对红卫兵和知青哥哥姐姐们景仰和崇拜”的后学们,他们觉得“那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充满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岁月甘泉》的宣传材料说:“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组成,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挥别亲人,在乡村垦荒、劳作、思亲、爱恋、迷茫、牺牲等等的历练和场景。”“自1968年以来,人数高达两千万的中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青春宝贵的岁月,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岁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时代那一段充满浪漫、悲壮、迷茫和欢笑的特殊生命里程。”《岁月甘泉》引发了海内外知青的尖锐批判:
“这部从主题、基调到语言、形式都像极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歌》的作品,把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比作‘甘泉’,高唱‘青春无悔’,讴歌知青时代的那场噩梦,是对绝大多数知青感情的粗暴践踏。”“作为广东知青,苏炜不会不知道当时规模浩大、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逃港潮,《岁月甘泉》最对不起那些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上山下乡运动的死难知青!”“到美国20多年,在这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观的熏陶下,还没有学会说真话!还要粉饰文革,歌唱邪恶!我为他们羞愧!”苏炜却振振有词:
“这部作品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代人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难以忘怀,而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知青情结确实是一种怀旧的产物,但怀旧却是一种因岁月流逝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确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视.。”“作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仅值得缅怀,更值得投注情感,诉诸歌唱和咏叹。”“对待苦难有两种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难、悲悲切切、唠唠叨叨、永难自拔;二是苏东坡模式,历经苦难、洒脱依然、大气磅礴、乐观向上。”“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把一切话题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谓‘文革遗毒’的最突出特征。当有人断言‘苦井里绝对只有苦水,绝对掘不出甘泉’之时,其实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陷于文革思维之中。”苏炜这是在强词夺理,显然,他在“缅怀”、“歌唱和咏叹”“岁月甘泉”时,带着浓烈的文革文化印记,却把文革的罪恶和苦难全都删除了。
《岁月甘泉》不尊重正视历史,用怀旧的情感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难演绎成对国家的救赎,企图以一代人的牺牲为知青赚取光荣,并幻化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它极力讴歌以青春为代价的所谓“磅礴”,将上山下乡运动涂抹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悲壮、崇高”叙事并定位,把幻灭的理想主义投射到失败的历史上,这是对当年众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亵渎,是对那些先为毛革命又为邓改革付出双重代价的弱势知青的漠视,是对无数被强奸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践踏,是对李庆霖告“御状”后毛“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否定,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白。《岁月甘泉》掩盖了历史,对罪恶的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它轻而易举地与历史和解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近四十年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锐对立;一直执掌着话语权的歌德派们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明真相,已经被成功地蛊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视野和思维都仍被局限在当局的意志之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缺乏独立、正确的判断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显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仍任重道远。
二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
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作品。
结果,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许多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对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三上山下乡不自文革始,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还知青谋生、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毛为了实现乌托邦幻想,不依经济规律治国,知青上山下乡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被强制,而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
下乡后我们才认识到,知青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是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
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当局抛弃、被当作牺牲品的。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的。更何况上山下乡期间,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并没起到什么推进作用,客观上没消灭多少三大差别,我们的思想也没有变得成熟。因而我们不是什么奉献、什么牺牲精神,不值得夸耀,更谈不上光荣。那些歌德者们大肆讴歌知青的“牺牲精神”是回避了制度之恶,是对专制感恩戴德,是用知青一代的牺牲为其恶果买单,是“被卖了还替人数钱”。
四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早在文革前,我们中一些出身不好的就被剥夺了或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即使我们受到的那些教育也是被扭曲的。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了,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只属于他們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我们却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以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为目的,个人的价值不被认可,人人都只是没有性别、没有特点、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意志的标准件。结果教育成了愚民的手段,我们这些受教育者成了没有独立意识、愚昧无知、任人摆布的棋子。
翻开我们那时的日记、书信、决心书、大批判稿、“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那极左的语言、傻冒的心态多么可笑、可卑、可怜、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文革初,我们对校长狠斗猛批、对老师揭发批判、对同学咄咄逼人、与父母划清界限、以破坏文物为能事、以把经典名著投入火堆为快;下乡后,我们批斗地富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这一切统统是我们这一代的群体行为,是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集体犯罪。
当然,我们只是参与者而绝非制造者,我们更多的角色是苦难的承受者。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从历史的角度,苦难只能是教训、是前车之鉴。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我们不能漠视,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些苦难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我们的苦难既源于罪恶的体制,也源于我们参与了罪恶,面对那段历史我们不能毫无罪恶感和愧疚感。
固然,上山下乡时我们曾付出过真诚,曾把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带到了农村。我们教过农村娃娃们学文化,我们用微薄的知识和顽强的自学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送医送药。。。,然而,我们不是也曾把阶级斗争带到重家族讲亲情的农耕社会,用丧失道德的偷鸡摸狗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我们与之争食、却接纳了我们的农民身上吗?我们那点有限的贡献实在难抵上山下乡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危害,更不用说这种传播城市文明的方式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下乡时确曾怀着革命理想,可是那时的所谓理想不过是被忽悠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今天我们还用那虚无缥缈的“理想”为自己辩护,那么面对社会不公时,我们依旧会从文革这个负资产中寻找思想资源,以专制的思维和造反的方式重蹈覆辙。
既然我们亲历了城市的和乡村的、上层的和底层的、反修防修的和拨乱反正的、闭关锁国的和改革开放的、破坏的和建设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乃至希望的和绝望的、宠儿的和弃儿的等等截然不同的体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思想解放、与世界接轨、更广阔的视野、对比和参照;有了较为独立的人格;那么今天回首上山下乡时,我们就真的“青春无悔”吗?
二战后,许多西方人无法原谅自己,用整个后半生忏悔赎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均特格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面对这样高尚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干系”?既然我们自认为曾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并至今为之骄傲,既然我们自诩是有着神圣使命感责任感的一代,那么是不是也该“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
可是,对文革、对上山下乡运动、对历史我们知青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却喜欢以知青的名义抱团取暖,过分热衷于各种单纯怀旧、缺少反思、甚至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曾是蚁群式的,没有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力意识,人人都不过是完全依附于群体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总是崇尚、依赖于知青群体而没有自我。我们一直不自觉地陷于集体无意识当中,这个劣根性是知青的突出特点之一,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中。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下知青是一家”。每当提到知青,我们或许有超越性别、年龄、地域、职业的某种亲切感,但我们很难突破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彼此认同。事实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由于出身、经历和政见大相径庭,天下知青根本就不是一家,“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胡发云)。
我们这代人曾深受泯灭个体意识的集体主义教育,我们的个体权利总是被整体利益取代。被孤立被抛弃的恐惧使我们有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很多知青直到老年仍渴望在知青群体里找到依靠,仍企图通过高唱“理想主义”和坚持“青春无悔”得到慰藉。
法国著名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说:“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苏炜的“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正反映了我们在罪恶环境中极易导致“集体犯罪”的“集体无意识”。他宏观叙事时敢于用错误的偏狭的个人感受代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评价,也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在有关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青难道不该进一步找回自我,重新认真审视我们的青春时代?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在以愚昧盲从为主要特征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到底能有什么价值?
在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集体迷幻中,“青春无悔”的依据究竟何在?
根本的问题是: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发表于《共识网》2015 7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