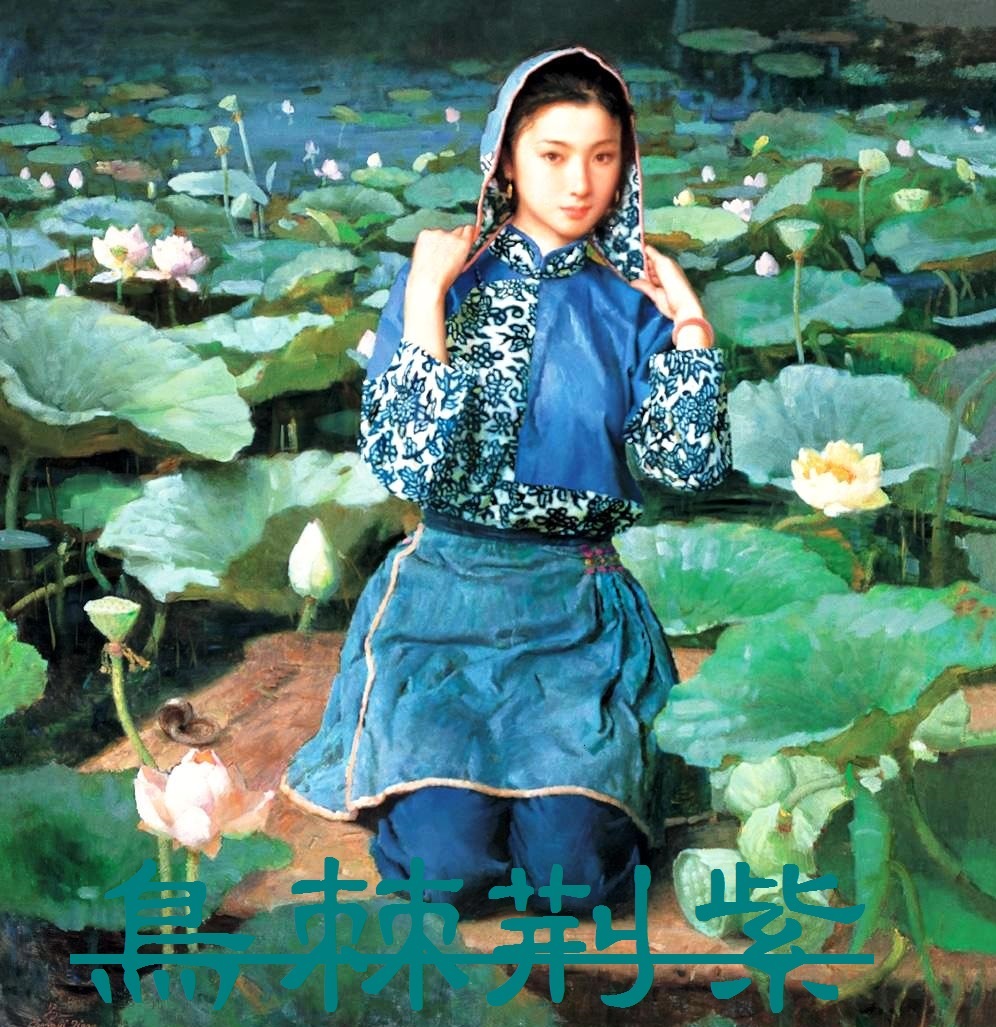闲侃(11):普通高学历海华 vs 高学历普通海华
前几天万维新警察(严格说来属于较新的警察)兼政治家、才女逸草同学,和退休咨询专家、起码货美国工科教授就“普通高学历海华” vs “高学历普通海华”哪个表达更合适这个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工科教授觉得前者更好,可能觉得逸草同学人如其名,性情安逸温柔,于是冒冒失失地上去提意见,没料到逸草性情刚烈,将工科教授臭骂几顿,将他的意见踢了回来。须知工科教授平素都是被学生花团锦簇着的,看到的是尊敬,收到的是贿赂,哪里受过这等窝囊气?于是草草搭了个擂台,和逸草展开对攻。工科教授招式威猛,但逸草闪避腾挪,见招拆招,竟然不落下风,双方竟是不分胜负。
一个是政治家兼才女,另一个是退休专家兼教授,双方都是高级职称,不在万维将“博士、教授、PRL文章”整天挂嘴边的 mingcheng99 物理博士兼社会学教授之下。到底谁说得在理呢?答案是:不知道。为甚马不知道?答案是:因为人微言轻,所以我们不知道。
但工科教授当天又举了些类似的例子,我们看看这些例子,看能否发现些端倪。工科教授当天吹眉毛瞪眼睛举出的几个例子是:“美丽的女护士、好男人、臭咸鱼、小铜佛、胖女人、优雅的女演员、细长铜丝……”都是恰当的表达,而“女美丽护士、男好人、咸臭鱼、铜小佛、女胖人、女优雅演员、铜细长丝……”则是不恰当的表达。很明显,除了“臭咸鱼”vs“咸臭鱼”比较 subtle 不是那么明显外,像别的例子,例如“小铜佛”vs“铜小佛”两者的优劣却几乎没有疑义。铜小佛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根本和我们的表达习惯相抵触。
佛像的两个修饰定语“小的”、“铜质的”,看起来是独立不相干的两个修饰语,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小铜佛”这个表达很自然、而“铜小佛”非常别扭?这其中必定有原因。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我觉得上次我留言所说的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铜质”和“小”相比,铜质和佛像关系更加密切,铜质可以看成是这座佛像的一种固有属性,不大容易改变。这尊佛像在大雄宝殿是铜质的,你拿回家供在神龛上,它还是铜质的,并不会改变;但这尊佛像到底是大还是小,这就难说的多,因为这是不同的人拿它和不同的佛像去比较得出的很主观的结论。也就是说,佛像是大还是小,这是个集约概念,和佛像的联系就没那么密切了。
大家不妨再具体看看工科教授给的其他几个例子,“美丽的女护士、好男人、臭咸鱼、小铜佛、胖女人、优雅的女演员、细长铜丝……”,除了“臭咸鱼”外,都受上述规则的支配。当然臭咸鱼也不和这个规则抵触,而是臭和咸一个涉及嗅觉一个涉及味觉,它们和鱼的内秉属性关系,看起来差不多。如果“臭咸鱼”看上去更顺口一些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和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有关。类似的例子还有图论中的“Red Black Tree”,大家之所以都说“红黑树”而不说“黑红树”,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俗成。如果最开始发现红黑树算法的人将它称为黑红树,那么今天估计大家都会说黑红树。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为啥和名词联系更密切的修饰语应该放在和该名词较近的内层、和该名词联系更疏松的修饰语应该放在较远的外层呢?这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具体原因大家自然可以各抒己见,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精确度”的要求。很显然,你将某个名词“佛像”抛出来,再加上两个定语限制,目的是什么?目的显然是缩小外延,使得你的描述更加具体特定,也就是更加精确。那么,是不是“小铜佛”就比“铜小佛”更精确、“好男人”会比“男好人”更加精确?我觉得是的。我们先看“好男人”这个更加简单的例子。我们假设人可以从性别分为男人、女人,各占50%;从品质而言可以分为好人、不好不坏的人、坏人三类,各占1/3。初看起来,“好男人”和“男好人”就表达精确度而言并无区别,因为品质、性别看起来是两个不相干的二维独立变量,但是,文字和语言作为描述的工具,它却是一维、sequential 的。记住此时“性别”是某人的固有属性,但“好坏”却不是,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某人是男是女是100%确定无歧义的,但其品质(三种品质)则是完全随机的,几率各占1/3。“坏男人”此时是修饰“男人”的,“坏”此时虽然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但其空间此时已经缩小了一半;而“男坏人”呢,此时占据三分之一几率的“坏”,其空间是则全部男女。
(我想这应该是原因,但好像不太容易写明白。哪位同学有更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