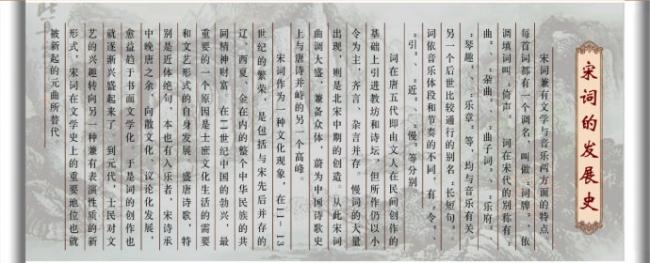说娼妓(六)歌妓与宋词
发表时间:+-
接上篇:说娼妓(五)歌妓与唐诗
有人说过:“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毕竟《全唐诗》将近5万首诗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诗与青楼有关)。“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大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到了宋朝,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与青楼的关系还要密切。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青楼女子和客人们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
其实词的起源很早,隋代就有曲子词。词在中唐以后得以发展,成熟在晚唐,五代,兴盛是在宋代,宋朝是词的时代。中唐后为什么会有新文体“词”的发展呢?说来也要怪唐代各位大诗人太“牛”。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也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既然诗已做尽,文人不再写诗了,或者兴趣根本不在写诗上了,都来写词了,“词”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说到“词”的发展,青楼女子和乐工们可谓功不可没。“词”,就是歌词,古代又称“曲子词”,它是用来唱的,谁唱,自然是青楼妓馆的歌女们。乐工歌妓们拿着格律整齐,字数一定的律绝句做歌词,很难与变化错综的乐调相配合。为了好唱好听,她们就应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作为歌谱,或在字的中间加“和声”,或在句子里面插入“泛声”,这也就促使诗人们“倚声填词”,不仅力求文辞优美,更要兼顾音律谐婉,无形中诗就慢慢变成了长短句“词”。
难怪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叶嘉莹也在她的《唐宋词十七讲》里谈到: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酒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相思离别的内容。”
词这种形式,典雅清丽, 语言工巧, 音调和谐,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宋词的题材很多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艳情”上。
词最初都是可以唱的,由于发展,以后慢慢就脱离了它的音乐性,不再唱了,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宋朝经济繁荣,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艺术文化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了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 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 各城市中都有歌楼妓馆, 贵族豪绅家中也多有歌妓舞女, 这些都促使“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弄得我们这些后辈只知有宋词不知宋诗为何物了。
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抒情主人公,并由歌妓演唱士人赏听,从而完成整个创作演唱接受鉴赏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妓在词的创作,词与乐曲的结合,词的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凭无据,咱可不敢乱说,信手一翻,此类词作便跃然纸上,举不胜举。
在宋朝的众多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柳永。柳永的一生穷困潦倒,直到晚年才中进士,只做过一些小官,他怀才不遇,知道自己一生与功名富贵无缘,所以他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词的创作上。他的那首《鹤冲天》,几乎就是他一生生活的写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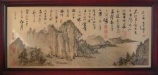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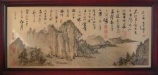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去便,争不恣游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落榜了,不考进士了,不做官了,要整天喝酒,逛青楼,做个专业词人。青楼里有他的意中人,那多快活!(其实柳永后来还是去考科举了,而且还考上了,被封了个小官)
柳永的调几乎多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帏淫媟之语”;柳永的词好多是在“浅斟低唱”中写成的;柳永的情多依于“偎红依翠”;柳永的创作素材也多取于“烟花巷陌”,所以“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在当时,柳永的词就是流行歌曲,“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风靡天下,无人媲美。柳词中有名字的歌女都不少:
秀香:“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昼夜乐》)
英英:“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柳腰轻》)
瑶卿:“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凤衔杯》)
心娘:“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木兰花》)
佳娘:“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
酥娘:“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木兰花》)
虫虫:“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集贤宾》)
英英:“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柳腰轻》)
瑶卿:“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凤衔杯》)
心娘:“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木兰花》)
佳娘:“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
酥娘:“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木兰花》)
虫虫:“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集贤宾》)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片恃俊。”(《木兰花》)
传柳永死后,据说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并且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宋代的大词人中,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姜夔等等都与歌妓过从甚密,并且写下了许多反映妓女生活的佳篇名句,这里也随便举几个为例:
晏几道的名篇《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写的是与一个朝思暮想的歌妓重逢时的惊喜之情。在小山词中直接提到名字的歌妓就有:小莲,小鸿,朝云,小苹(颦),小琼,师师,阿茸,念奴,玉真,吴姬等。小晏对她们动情,为她们写了大量的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虞美人》)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临江仙》)
小琼闲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清平乐》)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临江仙》)
小琼闲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清平乐》)
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写的是他的一往情深。
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写的是他的心醉。
姜白石的“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写的是他的心情。
苏东坡的那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人说这里的这里的西子,并非是指西施,而是伴随苏东坡游玩的妓女,不知是否属实。
提到宋朝,就想到宋词。宋词已成为宋朝的标志性符号。辉煌的宋词艺术,成千上万的传世名篇,那就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星光灿烂的宋词作者,都早已名留史册。如果说苏东坡是宋词豪放派词作者的代表,那么柳永就是宋词婉约派词作者的代表,宋词的起源是以婉约为始,虽然说有过苏东坡,辛弃疾打破了婉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启豪放一派,但他们只是“打破了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词婉约的风格。宋词仍然是以缠绵,婉约为宗。倘若宋词婉约派离了青楼歌女,就像鱼儿离开了溪水,也就没有了婉约派的“晓风残月”,“缠绵悱恻”,婉约派的词作便会黯然失色,辉煌的宋词艺术至少会失去一多半的美:“莫谓词人轻薄,正是词家本色”,宋词就是一杯清茶,需要慢慢品味,宋词就是涓涓细流,泉水叮咚,诉说的是卿卿我我,玲珑剔透,缠绵感人。
(参考资料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