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泥街》荒诞世界的精神解剖图
1.重读《黄泥街》的诸多理由

当年读《黄泥街》,倒也不算奇怪。长沙有条黄泥街,是书商云集之地,我当然光临过。而残雪写的《黄泥街》,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一个封闭而荒诞的世界,与现实中完全不搭界的。读过之后,认为是当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感觉它传承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文学传统,文中也有卡夫卡的影子,比如《黄泥街》中有两个似是而非的人物——王子光、王四麻,让我联想到《城堡》里的K先生,这并非没来由。
这次重读,这种感觉至今没有变化。
经典众多,要重读《黄泥街》,虽然是残雪出道之作,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亦如2025年匈牙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拉斯洛的《撒旦探戈》那样的处女作,皆出手不凡,在寻找中国作家出道即产生影响,残雪是个标志性人物,我被触动,唤醒《黄泥街》记忆。再重读她的处女之作,想到前年阅读的《黑暗地母的礼物》,可与她初期之作做个对比,这估计也是原因之一。再是残雪在海外的声誉,以及她一直被认为国内诺奖“陪榜率”最高的作家(不排除国内出版界和媒体乐此不疲把她作为话题),圈子中有人不时谈及残雪,会用一种知音难觅的口气加一句,读残雪是有门槛的,确实如此,有位与残雪交好的作家曾说,当今懂残雪小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她本人,一个是她的哥哥邓晓芒,还有半个人就是这位作家了。读到后边,无法分辨叙述的事件、人物、情节,更不说故事的起伏,甚至连脉络也失去了,完全浮光掠影意象,只能跟着感觉走。然而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在暗夜之中茫然四顾摸索的写作者,需要了解各种文学流派,至少为我所参照和借鉴(有时我会为这种自觉探索和尝试而感动)。再读,也想了解自己文学鉴赏能力是否有点长进。重读一部作品,居然要找如此多的理由,一个人如此拧巴,说明本人也够偏执的。
个人认为,读不读懂残雪是一回事,读不读残雪又是另一回事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她的作品对中国传统以及现当代文学皆具有颠覆性,这种独树一帜的探索性,皆是十分可贵的,值得学习和肯定的。她受到西方文学界的推崇,也足以说明她已经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2.现实世界末日场景真实呈现

《黄泥街》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恶之花”。这个名词源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诗歌代表作,我理解是放大内心之恶,开放恶之花,它是不是与《黄泥街》有同工异曲之妙。
看看残雪笔下的场景,天上的太阳,长年是昏黄的,像个挂在天上的一个球,没有日出之美,也难以让黄泥街人看到落日时的气势。别以为太阳没有能见度,就少了酷热,这里的房子,就像建在蒸笼锅里一样;太阳下的光景,一切都在腐烂之中发臭:菜市场的变质霉烂的菜蔬冒着热气,渗出的黄水流到街道上;人们卖的水果全部都是烂的,即使是烂的,他们也吃不起;太阳出来时,家家户户争先恐后挂出烂鱼臭肉晾晒,空气中混合进恶臭,长年被捂着人体周身弥漫的体臭,加之百岁老头小腿上溃烂流脓,同样连卖猪肉者背上烂出的洞孔能流出猪油来——这种腐烂达到何种程度呢?人被化成血水,如果邮政车停在黄泥街半个钟头,也会被烂掉一个轮子。
酷热之下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极端,它一旦陷入了雨季,就会落它个七七四十九天无法收场,那雨常年是飘落下来的墨黑灰屑,咸腥如汗的黑雨,缺少地下管道的循环,无法疏通,积在街上汇成污秽肮脏的河道,人们习惯把什么都往这河道里扔,连将死的老人,用破絮一裹“扑通”一下扔进去,死猫死狗死婴的浮尸在水中漂浮。
所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绿头苍蝇嗡嗡之声不绝于耳,遮天蔽日的蚊虫汹涌而来,肥硕的蟑螂随处可见,蛞蝓(鼻涕虫)在墙壁上灶台上所有爬行处留下晶莹透亮的痕迹。屋顶温热腥臭的茅草随时掉下来,家里发霉房梁屋顶长满的黑色毒蘑菇。黄泥街的天气比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马孔多的暴雨更让人恐惧。
这里的人与外界隔绝,有人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一步,尽管城市近在咫尺,他们也难得迈出一步,成了一个对外隔绝的孤岛,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
黄泥街最值得炫耀之处,即作家多次提及过一个S机械厂,厂里有五六百人,我们难以听到机器轰鸣声,他们除了陷入没完没了的学习和汇报外,再就是习惯昏睡,最后落到实处就是生产钢球,这些钢球用于什么,没人会关心,大概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需要完成。
黄泥街的人不管多么酷热,都要穿着棉袄,戴着棉帽子。使我想到从前小镇上用自行车驮着箱子卖冰棒的人,用厚棉衣包裹冰棒,使它不容易融化。这些居民是不是认定厚衣物,可以抵御污染就不得而知了,或者怕被暴眼的剃头匠割去了耳朵,就这样沤着捂着,于是有的人肚子烂了洞,流出脓血之水,所有人的躯体浑身上下成了细菌和蚊虫繁殖的场所,大部分人都长着一双烂红眼,眼药水特别畅销,当然也有人发明了屋檐水可治眼疾,这要等天落雨。
黄泥街的人只要等雨一停下来,便像一只只老鼠从暗黑洞孔的破房子钻出来了,三五成群,发出“吱吱”之语。黄泥街在这种恶劣天气和环境中,是植物动物生长的天堂,更是真菌类的植物绝妙之地。有的人家屋顶床底下养仙人掌,有的人厨房里长出了柚子树,至于黑色的各种形态的无法食用蘑菇随处可见。倒挂在房梁屋顶的蝙蝠与人和谐相处,墙体上成了壁虎根据地,更有甚者一群老鼠围攻并咬死猫。至于蛇鼠蚊蝇,蛆虫蚂蚁,还有水中的蚂蝗随时爬到人体吮吸,蜥蜴更是不期而遇,一些古怪生物的出现让人麻木到视而不见。
人的日常就是吃喝拉撒,他们长年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之中,加之厕所太少,街道被淹,住在阁楼上的人们,便把地板挖个洞,就这样拉屎撒尿,人人是一个个病原体——拉肚子、溃烂生疮,身体上流着脓血水,生蛆长虫,感染的伤口灿若桃花,长疖子就是平常之事;长久浸泡人体变异到许多人脚上竟然长出了鸡爪子。
他们的饮食千奇百怪,试举一例,作者这样描述:“齐婆踱过来,踱过去,将铁门弄得响个不停。有时又忽然大步流星,窜到一个没人的黑角落里,睁大了老眼瞄来瞄去。瞄过之后,发现没人,就跪下去大啃一顿泥巴,嚼得满嘴泥沙,吱吱嘎嘎地响。”齐婆的行为倒不算怪异,宋婆捕捉到蝇子了,除掉它的绿头,剪掉它的翅膀,放在锅里炒着吃,尽管她的男人用尽各种办法制止,她还是乐此不疲。张灭资吃了水中漂浮的瘟鸡,一命呜呼。有人双脚踩踏蟑螂,积成厚厚一层,而那些生吞活剥蟑螂之人,更是家常便饭了,原本出现在阴暗潮湿之地的鼻涕虫,纷纷挤占着人们的生存空间,这一切就是黄泥街人的生活常态。
这是不是一幅立体的“恶之花”图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作者有意让我们吃不下饭恶心的描写,在我看来,残雪用一种写实主义的手法,放大展示的这个现实世界,看着荒诞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当这些文字呈现在我眼前时,我脑海里回忆起幼年在故乡的场景,春夏之际,一场场的豪雨瓢泼桶倒下着,整个湾台淹在洪水中,最初雨水清澈,幼年的孩儿拿着簸箕渔具就在家中厅堂捉鱼,哪知几个时辰过后,屋前房后的茅厕沤成沼气,湾中四周的垃圾场在雨水中漂浮,死鱼死猫死狗尸身上叮满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整个湾台弥漫着腥臭难闻的气味。
长大了,到城市里工作,走到十余分钟就是一个著名城中湖,早年尚可在此畅游,不知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城市的下水道,湖水浑浊,白色垃圾障眼在湖中沉浮,而一些动物尸体随处可见,在湖边行走的人们,皆是掩鼻而过。有一日早上我路过时,一具死尸肚皮鼓胀,手脚四肢朝天,像在呐喊又像有冤要伸。还有一些离湖不远的城中村,人流汹涌,各种吃食的香味掩盖不住污秽之气,疯狂赚钱的小商小贩,从凌晨忙碌到夜深,汤料中浮动着蟑螂身影,老鼠大白天在人缝里觅食,一幅幅末日的饕餮景象,在脑海里晃动,没有节制,也无法管控,它与作者笔下的黄泥街半斤八两的差别。
我们人类是一种极强的适应性动物,这叫“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3.集体谵妄中的人性困境

如此不堪的环境之中,加上许多应时的背景,构成了黄泥街一道特殊的风景。
黄泥街的人们一直处在“政治挂帅”之中,强调思想觉悟要不断地提高,和政治面貌清白,被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怀疑、调查、逮捕,上级下发指示,群众定期向上汇报思想,以及敏感之人莫名其妙的失踪,和似是而非被牵扯出来的人和事,所有人在污秽的环境中呈现出病态的亢奋。整篇《黄泥街》中,不断穿插着许多时代特定时期的用语“百万人头落地”“狠抓党内一小撮”“张灭资”“目前形势好得很”“委员会”“革命老区根据地”“领会上级精神”“社论学习”“有一个黑影,同志们不要大意”“《闪闪红星》”……之类用词,看似荒谬,实则是一种现实的映射。
《黄泥街》没有主角,杨三癫子、老郁、区长、齐婆、王厂长、李大婆、朱干事、胡三老头、王九婆、齐四爷、隔壁宋家、造反派……居民共同构成“荒诞的主体”,人物跳跃性的进入或没来由消失,似乎作者着力制造这样一种碎片化的效果,其怪异的行为与心理暗藏多重隐喻。精神状态的扭曲与瘫痪,人们热衷于沉迷毫无意义的“研究”与争论“王子光是人还是东西,他是否存在?”“王四麻是谁?他是区长?还是流窜犯?”大小便随处可见,把张灭资的空屋子当成茅厕,无所顾忌地拉屎撒尿,却热议厕所拆迁、垃圾站治理,只能是永远停留在泛泛的空谈之中,并无实际动作,人与人之间彼此抵防、警觉。这种在时代大潮里的变奏,隐喻着一个黄泥街人这个群体在困境中的无力突围。
还有一个特点,个个噩梦连连,人人皆被凶兆梦境缠绕,各色人等皆热衷梦呓,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散播恐惧,将潜意识里的焦虑转化为集体绝望之情。作者这种书写就是一种“黑暗灵魂的舞蹈”,在无望之中暴露被理性压抑的真实创伤。
所有人表现出的淡然与冷漠,便是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宋婆将父亲的尸体塞进纸箱抛入河中,只是留下水花一溅,居民对下水道的惨叫、防空洞的躲藏,被割下耳朵失去听力同样习以为常;动则以一句口号定人生死,抓住小偷,捆绑吊打以私刑则成为所谓“正义”的替代品。死亡在这里失去重量,就是残雪笔下“狞厉的抒情”——不渲染悲伤,让人窥见伤痕,只展现死亡的卑贱与恐怖。
当烂水果都成为奢侈品,道德便沦为生存的牺牲品。居民们吃瘟鸡、捕蝇子的行为,实则是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异化标本。
“王子光”作为《黄泥街》的核心谜团,他却是在作者笔下真实地出现过,然而在居民口中,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有人说他就像《圣经·创世纪》中“要有光”的隐喻,绝望之中,所有人找不到那束光,这个是否存在的人物,成为黄泥街人群体谵妄的载体,暗合特殊历史时期的谣言与猜忌。
机械厂的钢球,是否呈现出历史的硬度;堆积如山的垃圾,是不是现实的腐殖体;黑雨里的浮尸,更像是人性的变异。多种意象交织构成“历史沉重与现实腐败”的隐喻,我们分析,它使黄泥街人成为中下层阶级精神困境的象征。
4.我对隐喻同样情有独钟

记得幼年,有次我的外婆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之后,昏死两天两夜醒来,她讲起一个巨大的龙船把她接走,“前面有洋鼓洋号开路”(我清楚记得这个表述)。过后,她不断重复讲着这个故事,有次我听她说,她在少年时便做这个龙船之梦,对我深深地触动,是我以她为原型创作的重要契机。我在《四十岁的一对指甲》里反复呈现这艘龙船,它是不是驶往了天国,我实在不甚清晰它是隐喻什么?倒是不少读者对它做过解读。《云梦泽》中那个湖滨酒店的尤老板(连着他的姓也少龙一撇),是一条失去水源正在修炼蛟龙,因为云梦古泽干涸,一时无法回归向往的天空,不得已只好化为人身。它被隐喻为大自然的杰出代表,当人们肆意妄为破坏自然环境时,它与人抗争之时,从未停止反抗。在《丢失了的城池》三部曲首部《绣船一号与雄起城》中,水上丽春院隐喻着原始生命力被资本和权力规训扭曲的过程;在第二部《无影人与雄起跃进城》中无影人组织,隐喻着对激进理想主义与权力哲学的深刻反思;在第三部《小妖精·影与雄起实验城》中,将视角聚焦于社会转型期的乱象、技术异化与个体挣扎,将科研引向乌托邦式歧途的荒唐实践,以及金搭子荒诞却深刻的“城市毛病学”,隐喻着对科学规律的僭越和民众对时代变迁不适的精神焦虑。
在构思时,我未必清晰这些意象到底隐喻着什么?我想构思是一回事,创作又是另一回事,相信创作的成败,还是要跟着感觉走,只是无法像残雪这样走得过于遥远。
我更注意到《黄泥街》的创作,鲜明体现了其文学特质,即借鉴西方后现代手法,以碎片化叙事、超现实意象剖开心理深层结构。如“焚尸炉烟灰像雨飘落”“死鼠在地面腐烂”等句子,将丑恶与诗意并置,这同时承接了波德莱尔“恶之花”文学传统。
一个成功的作家,立意定会高远深厚的,它在主旨上的“民族寓言”是黄泥街的封闭性对应“沉睡的中国”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居民的麻木不仁更是呼应着鲁迅先生“国民性”的批判。曾有评论家指出,小说对红色运动记忆的变形处理,与西方现代派技巧结合,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先锋文学的里程碑。
在重新阅读《黄泥街》时,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杨林老谢《老实说,残雪根本代表不了东方文学去争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引发读者的热议,残雪早已成了一个话题,时不时被人勾起来。在我看来,她能不能代表东方文学,应该是个伪命题。从她的文字里读到我幼年许多熟悉的肮脏的场景,那些漂浮的死尸,蟑螂、鼻涕虫、绿头苍蝇、蚊子,茅坑、粪桶,这就够了。
我曾向一位文学教授表述过一个观点,残雪是用西方文学流派之瓶,试图装现、当代几十年社会变迁和时代“混合”之酒。她的文本读来让人不适甚至很不舒服,有时要硬着头皮去了解,意象过多,支离破碎,漂浮的灵魂梦呓。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无法回避地重复自己。然而真正读进去时,也有一些感觉,耐人咀嚼,意象独特。
不管是村上春树,还是残雪,都是我注意的作家,也认真拜读过他们的大作,这些年来一直追踪诺奖之作,就有一条,在同一领域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并卓有建树,就达到获评奖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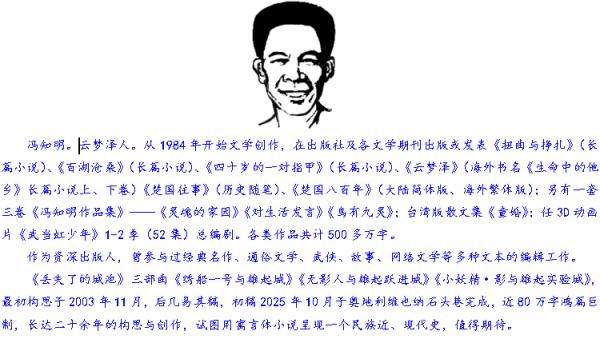
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 法兰克福美茵河畔40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