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赏析
姜夔《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赏析
历代名家名词赏析之六十六
王能全

我思我在摄影
《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南宋】姜夔
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词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
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
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
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
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
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这是一首咏物的名篇,借描写蟋蟀凄鸣,书写人间离愁别绪、幽怨遗恨。由词序可知,这首词作于丙辰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张功父,即张鎡,先赋《满庭芳·促织儿》,写蟋蟀之形;姜夔则别开生面,咏蟋蟀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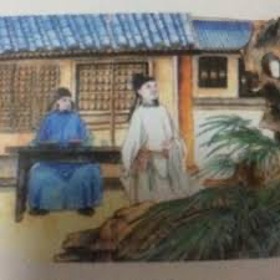
上片的前半段以庾郎为代表,写文人墨客听蝉鸣之感。庾郎:庾信(513 - 581),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曾作《愁赋》等。杜甫写有诗句:“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这首词的开头两句:“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忧忧不得志的庾信正在自吟悲伤的《愁赋》,又传来凄切细碎的蝉虫私语,心中更为凄凉。“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铜铺”:古时门上铜环的底座;“伊”:蟋蟀。露水浸湿的铜铺,沾满青苔的石井,都曾听到蟋蟀的凄鸣。无论在书房,还是在室外,“寒蝉凄切”,这声音弥漫在秋色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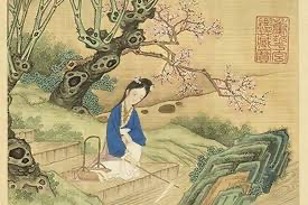
接着,以蟋蟀的“哀音似诉”承上启下。蟋蟀,因其鸣声响如织布机,又名促织。促织如诉如泣的哀鸣声,让本已辗转难眠的闺中女子更加无法入睡,只得起床,以织布来排遣心烦意乱的思绪。作者巧妙地将蟋蟀的别名化入词意,秋蝉的凄鸣声与机杼声融成一片,深刻地勾画了思妇的孤寂和苦闷。“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织布女子面对屏风上的山水景象,挂牵和眷念着远方的夫婿,何时方能将亲手织就的冬衣送到他的手中?何时他方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深秋寒夜,独自一人,闺妇提不起任何情绪来自我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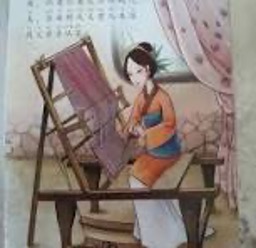
下片首句“西窗又吹暗雨”,运笔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地将词情进行了场景的切换,空间上从上片结尾的窗内移动到窗外。西窗外,夜深沉,风雨交加。再由户内的织布女换成井边的洗衣女。“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砧杵”:捣衣石和棒槌。那秋蝉究竟为谁断续不止地悲吟?与它相伴是不远处井边的阵阵捣衣声。接下来,随着蟋蟀鸣声由近及远,场景的空间、时间以及人物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沉郁悲切。“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候馆”:迎宾候客的馆舍;“离宫”:皇帝外巡时的行宫。秋风萧瑟,候馆内的游子迁客;残月高悬,离宫里的皇帝妃子;他们均是匆匆过客。秋去秋来,只有那候馆边、离宫外的秋蝉之声,年年细诉着人间无数的伤心之事。

紧接着词人妙笔一转,以乐事写悲情,蝉声更苦。“豳诗漫与”,“豳诗”指《诗经·豳风·七月》,其中写有蟋蟀的诗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词人先是自语,《诗经·豳风》中的《七月》曾经描写过蟋蟀,我被蟋蟀的鸣声感染,诗句率意而出。于是,写下貌似调侃的词句:“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可笑世上那些天真无知的孩子们,他们蹲在篱笆的角落,兴奋地呼喊着:快拿灯来,捉蟋蟀!清代词人陈廷焯对以上两句做了极为精辟地点赞:“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白雨斋词话》)词的最后点出主旨,“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有谁知道,如果将秋蝉的鸣声谱成琴曲,弹奏出来,一声声将是何等的凄苦!

南宋末期词人张炎在《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这首咏物之词,充分展示了姜白石精湛的艺术造诣。序文与正词,上片与下片,以蟋蟀之声一脉相连。作者发挥超凡的想象力,由蟋蟀的哀鸣声,联想到古今不同层次人物的悲苦。意象回转,层层递进,浑然一体,极尽情思、文采、声韵之妙。正如晚清冯煦对姜夔词作的评价:“天籁人力,两臻绝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本文取自作者的著作《词苑漫话–常用词牌及其历代佳作赏析》
此书已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正式出版
文中图片均取自网络